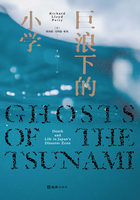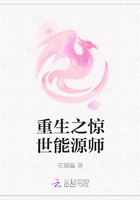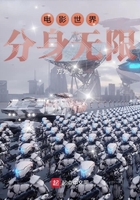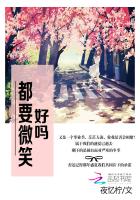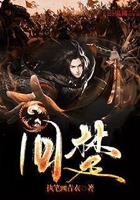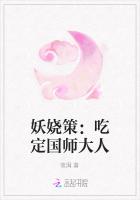汪文勤九岁从文,十四岁开始发表作品,她散见于国内外重要报刊的诗作,有数百首之多,其他尚有小说、散文、戏剧(主要是电视剧)陆续问世。若论写出的诗的积累存量,何止千首。据我了解,光是未整理的就可装满一皮箱。这些诗,基本上没有发表。她发表的态度十分保守,从未像很多人那样进行专门的包装和推介,原因很简单,因为她从来不认为自己已经正式开始了创作。事实上她的文学阅历十分丰富,一九六三年出生于新疆哈密;十六岁考入新疆政法学院学习法律;稍后,在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文学;一九九二年调入中国北京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任编导;九七年移民加拿大,现居温哥华,专事写作。在这之前,还在香港、美国、旧金山居住过一段时间。在海外漂泊的日子里,诗的写作从无一日间断。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抒情诗集《汪文勤诗选》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受到批评界的重视和读者欢迎,近年写作更勤,产量极丰,只是不常发表。对于这样一位作品曾多次在国内外获奖而犹谦称自己是初学者的作家,我是充满敬意和好奇的,我认为她厚积薄发,潜力无穷,是中国新诗新生代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等到潜藏期过去,她必然会在汉语诗的地平线上挥出一面光辉的标旗。
我曾长期对汪文勤的诗艺发展进行过观察,也细读了她发表过或未曾发表的作品,自认对她的诗和诗观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谨将我的心得综合为下列四点,提出来就教诗坛方家。初见一位天才的喜悦,好像天文学者自遥远天边发现一颗等待命名的星星,这正是我撰写此文时的心情。
一、古典与现代的融合
汪文勤认为盲目拘泥地对传统的抱残守缺,只会徒然滞塞了文学的正常演化与开展。中文系出身的她深深体认到,在后现代女性书写文艺新思潮漫天挥洒的今日,全盘西化固然不可取,但中国诗无法自外于世界文学是无可置疑的。她的诗,无论意境创造、结构组织、语言设计、意象经营,都希望做到在技巧方法上作横的移植,在历史精神上作纵的继承,抒写真正具有中国人精神质量而蕴涵现代意义的诗作,既不贵古贱今,也不以今非古,在同情的谅解下反映现实的氛围,在执着与追求中建构自己的诗风。她要求自己的作品,对传统中陈腐的部分产生刮垢磨光的作用,把古与今、新与旧的优质成分融一炉而冶之,惟有这样,才能把汉语诗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汪文勤集大成的文学理念,正符合大海不辞细流故能成其深广的道理,而更重要的是创作的实践,要不停地写,大量地写,才能在实战经验中找到现代汉诗新的门径。一首诗的完成、一本诗的诞生,胜过学者千层万面的空泛讨论。在这样的自觉下,她写了《老华侨》、《绿茶》、《医治诗心》、《三晋游吟》等一系列表现中国心、乡土情的作品。
二、抒情精神的掌握
中国诗自诗经三百篇以降,形成可贵的抒情传统,古人早已把诗的叙事功能让给了戏曲,以提高诗的纯粹性,尽量少写事,多写人,呈现心灵、性情,才是诗的精华所在。小说、散文、戏剧,往往是作者人格的间接转化,只有诗、抒情诗,才是作者人格的直接呈现,中间没有缓冲,也无从隐藏,它是“暴露性”最大的文体。汪文勤信守诗贵乎诚,首先不可失信于自己,心口不一,那就是妄语,是诗的大忌。她主张把生活感情加以概括,自自然然流淌出来,不见技巧只见性情,才是上乘的诗法。读汪文勤写边陲岁月的诗,每每有一种轻盈的风貌,她不喜欢壮言慷慨,故作载道,只把心中真正的感思诚实表达出来,做到信达,才是诗的雅。汪文勤作品还有一个特色,那就是诗行的有机性调节。为了控制抒情的张力,使一首诗不失之于过分压缩,她喜欢在诗中渗进一些散文的成分,以产生平衡作用。她认为诗句是密(实),散文句是疏(虚),她最注重虚实疏密的配置,常常采用赋格式的交替进行,以提高作品的审美效果。汪文勤说“语不惊人死不休”被很多人误用了,这句话只是对意象重要性所做的强调,如果真的句句密集安打,那就给人无法喘气的窒息感,也不成其为诗了。汪诗的抒情基调是避免紧张,尽量松驰,在浓烈与素淡之间,她宁愿选择后者。试读她的《七月八月》、《粉红》、《二月》、《传真给子扬》、《梦里天宽地阔》,就可领略她的艺术趣味。
三、佳句与佳篇并重
六十年代的台湾诗坛,诗人们往往为了重视佳句而忽略佳篇,每句每行务求险奇新异,结果严重影响了诗的传达。读一首现代主义的作品,处处碰到拦路虎,有时候简直无法通行。中国大陆近十年来的诗,也偶有这种情形,不过在程度上轻多了。根据我大量阅读汪文勤作品所得到的印象,她在谋句谋篇之间是有所选择的。她希望佳句佳篇兼而得之,但如果必需于二者选其一,她宁可属意谋篇,为了整体美学总效果的精准,放弃句式的雕琢,特别是那些失之于芜蔓的所谓佳句,以免以辞害意。细察汪诗,每一首都有冷静的设计,符合一种古典精神,而平实易懂是她最大的艺术要求,炫才唬人的文字游戏,她视为文学的败德行为,绝不为也。一般来说,汪文勤长于谋篇,有些诗呈球状结构,里边有严谨的组织肌理,丝丝入扣,审美效果十分集中。这种表现,可能跟她学过法律有关系,她曾制作大量的电视节目,或许也有影响。读汪文勤较长的作品就可发现,有时她是以制作的态度来治诗,诗想在形成之后,既经过慎密的安排,而又看不出刻意为之的痕迹。作为一位女性诗人,她的诗有时候有一种反闺秀的气质,不会喃喃梦呓,作我见犹怜状,更多的时候流露一种爽朗的英气,且以反讽语气批判人性的幽暗与软弱,但都是悲悯的,关怀的,绝少疾言厉色的抨击,且有时是通过现代剧场的手法,使人不知不觉进入她的思想核心,为其说服。这样戏剧感十足的表现方式,是她前一代或同代诗人比较少尝试的。她这方面的成绩,可以《伸手可及的禁区》、《回乡证》、《意守丹田》等诗为代表。
四、崇高感与伦理精神的阐扬
如果有人问近二十年两岸三地及世界各地华人的诗坛,缺乏哪样的素质,我要说,崇高感。崇高是美学中的重要品质,中外古典文学之所以肃穆宏伟,就是她具有崇高感。崇高感不一定符合道德规范,道德规范因时因地随时会变,但却是符合道德精神的,道德精神放诸四海而皆准,永远不会改变。伟大的作品,总是含有道德意识的。我们不妨以美、思、力三种素质来衡量汪文勤的作品,分析她在美感的迭现,哲学的深度与动人的力量上深浅轻重的掌握能力,会发现这三种素质,决定了她作品的一贯风貌。这种风貌的源头,乃是来自乡野生活,来自泥土的亲和力,所谓人在田园里,心系自然情,咏而歌之,自然纯朴厚实,动人心弦。汪文勤是大地的女儿,新疆的草原河流永远是她艺术的梦土、心灵的原乡,有了这,她的诗才能直指本心,写出人性的共相,触及人性的本然,使读者会其心而同其心。这便是所谓的伦理精神,伦理精神和崇高感是分不开的。诗要表现这两种感情,不外放歌与沉思,或放歌与沉思交替吟咏。少年时代醉心于美感经验的传达,是放歌;壮年放眼于社会的参与和责任,介于放歌与沉思之间。出国侨居这些年,汪文勤深入宗教灵修生活,着力探索生命哲学的玄思,这是沉思领域的浸淫了。但不管是放歌与沉思,母亲、大地和百姓仍是她一贯表现的三个向度,也就是伦理(从亲情、爱情、友情到民族之情)的泛写书。她这方面的作品极多,也是她作品中最深刻、思想含量最丰沛的一部分,其中有一首《捉迷藏》写对亡母的怀念,发表在美国《世界日报》副刊上,引起广泛好评,我认为是今年我读到最好的一首思母之作。同类型的作品还有《每个村头都有一条恒河》、《我的麦加是你的所在》、《在背阴的那面山坡》等,都有高层次的艺术表现。另外,她还有不少爱情的诗,也真挚感人。她情诗的独到处,是把男女之爱(不一定限于婚姻),提升到伦理的层次,这,乃是纯东方的、中国的境界了。
“小松犹百尺,少鹤已千年”。知道了汪文勤的创作生活背景,读了她的诗,对于像她这样一位写诗逾千首为文近百万言,犹谦虚说自己写作生活尚未开始的人,我不禁想起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台北外双溪书斋中的那副对联。如此百尺小松、千年少鹤的自我沉潜功夫,才真是所谓的大器晚成吧。
爱,是我能听懂的唯一语言
——汪文勤诗集序
洛夫
“爱,是我能听懂的唯一语言。”这是女诗人汪文勤一首诗中的句子,当我读过她寄来嘱我为这个集子写序的原稿时,忍不住想把这个句子改写为“诗,是我能听懂的汪文勤的唯一语言”。其实,如果要完全读懂一个人的诗,尤其是艺术感染力强而想象力丰富的诗,谈何容易。当然,我无意说,好诗就一定难懂,但如说一首语言无味、意蕴浅薄的诗极可能不是一首好诗,想必有识之士定能接受。我一向认为,诗之不同于其他的文学类型,主要在于它异于流俗,风神独具的个人风格,以及带有少许暧昧意味和陌生感的意象。这或许正是本质上诗不可尽解的原因,诗,毕竟是一个诗人的心灵密语。
以上只是个人对诗歌的偏见,并不是对汪文勤的诗作出定性的评述;我觉得她的某些诗如《胡杨十二月》的确有着个人心灵密语的成分,但她大部分的诗是可感可懂,可以引起大多读者的心灵共鸣的,原因无他,只因她能听懂和能传达的语言正是具有普世价值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