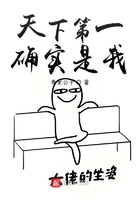他在水伯伯面前应下会照顾水色,如今水伯伯不在了他自然不能做背信弃义之人。可是为何他的心底却没由来的失落,有种挫败感油然而生。他在期待什么?他难道是期待她不是她吗?甩甩头,任风把思绪越吹越乱。
长夜漫漫几许清明,几许愁苦。白净已经记不起他这是第几次掏出那封不伦不类的休书了,终于还是没再多留恋,随手就要毁之。却在握拳时扯到了伤口,白净皱眉看着深深的渗着血的齿印,又想到了水色横了心的一踢,笑了。你咬我一口我还你一口,你踢我一脚似乎还欠着啊,想了想又重新将已捏成团的休书展平,收入怀中。
果然是这样,也未尝不可。既然你已不是原来的水色那么你踢我一脚我要你一生吧。
隔日一早,天还未亮。水色拖着睡眼惺忪的绿丫赶到未名居,姑娘们早都起来梳妆打扮了,未名居门前高高挂起了红灯笼,阿寺不知打哪里找来了一些红绸红缎镶嵌在楼里楼外,看上去非常的喜庆。
水色满意地点了点头,看样子昨晚绿丫口水没有白白浪费。姑娘们都住在楼上,打杂的住在后院,通向后院的门再封上仅留了一道小门供端茶倒水。行啦,水色站在水榭之上,举目四处望了望,一切安排妥当,就待群芳扬艳了。爬到楼上,选好位置坐了下来。不经意中扯动了肩膀,带着些许的疼痛,水色暗自骂了句粗话。真是憋屈,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也不回水府了。
天刚亮,厨房里就开始叫嚷着用餐了。水色一点儿也不担心没人来,早在前几日,这未名居外面就有人围观了,所以她连宣传也省了。手里头就留了二千两银票,其它的都交给了绿丫去打点。于是整个楼子里就看到绿丫忙得团团乱,水色在楼上嗑瓜子喝茶,等着看姑娘们的好戏。
其实老天待她也不薄了,水色感慨万分。捡了现成的便宜也该知足了啊。笑了笑,她终于开口叫住了已经在下面晃了不下十遍,脚步凌乱的绿丫。
“小姐!”绿丫忙得焦头烂额,哪知她家小姐就这么悠闲稳坐楼上。
“绿丫啊,不是招了那么多打杂的吗?你交待他们去做就成了,凡事都要亲力亲为挺累的,你说是吧!”
绿丫眨巴着眼,点点头。她确实是挺累的。水色又说:“你看啊,专门安排个人在门口迎客然后领到位上坐好,端茶倒水的跟后院里的区分下就好了,怎么会跑前跑后呢,一天下来那不是腿都短了?”
绿丫拍拍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就这去安排!”
“等等,你看客人们都陆续进了门了,先找几个姑娘出来撑撑场。还有,让阿寺到水榭后面去,万一有人闹事也在及时应付啊!”
“明白。”绿丫转身就走,才踏出两步又转回来,“小姐,那我呢?”
“你要去收银子啊,”水色郁闷了,“那,你看你看,这茶水钱要给吧,客人打赏钱要有人收吧。你还要嘴着甜儿,把客人都哄着开心了,要专挑好听得说啊。你看,你怎么可能没有事情做!”
水色说得很无辜,绿丫越听心越沉。早知如此就不该抢了小姐的事,不对不对,应该的!应该的!哪能让小姐抛头露面。
绿丫走后不久,姑娘们就鱼贯而出了。跟她预期的一样,眼见着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姑娘踩楼而下,水榭下面就开始骚动起来。水色记得有这么一句诗,“翠袖低垂笼玉笋,红裙斜曳露金莲”原本就是青楼出身的女子,自然是知道如何取乐于人。轻歌曼舞,衣袖低垂,肢娇腿柔。水色坐在楼上靠着窗,倚着栏,看得很清楚,琴声响起时,个个翩翩起舞,红黄白绿,各有各姿。饶是她早就见怪不怪了,也会有些惊艳。
水色又一想,若是有些灯光的作用就更好了,昏暗撩人,多有欲拒还迎之意,但是这也只能在心里想想作罢了。古代要用灯光挺难的,蜡烛都不知要点多少,浪费啊!
“这位爷,您也是来捧场的?”
“早就听人说东街茶楼关门待整,里面乒乒乓乓的。这不,来凑个热闹呐!”
旁边的人听了这话,也跟着凑了进来,“就是就是,前些日子这茶楼原来的秋狄掌柜的回乡了。那天我还跟他聊了几句,听闻收这楼的是位夫人,样子挺和善的。你们知道吧,秋掌柜这两年守着这破楼亏了不少,听说那位夫人出手大方的很,就不知以后的生意会怎么样?”
“大方又怎样,”另外一人不服了,“你看看,这还叫茶楼吗?台上那些不是万花楼的姑娘吗?什么未名居,听着新鲜不就是个青楼嘛。说不定这老鸨子还是从前的那个!”
“哎呀呀,这位爷。来喝茶!你们有所不知啊,万花楼的老鸨子还在大牢关着呢,她哪来那么大本事。窝藏逃犯那可是死罪,除非啊……”
众人被撩拨起来了,偏偏说这话的人调人口味,一脸猥 亵之相。有人就急了,“哎,你倒是快说啊!”
“除非那老鸨子跟咱梧桐县县太爷有染!”
“切!”
众人一哄而散,这年头什么谣传都有。水色趴在栏杆上,又将椅子往边上挪了挪。
“哎哎,你们可别不信啊,”那人急了,端起茶一口灌下去,抬手左招右揽,“那你们看看,这台上姑娘可有眼熟,那不都是万花楼里的嘛。说不定啊,那红儿姑娘也在呢,哥儿们要不要咱们赌赌。”
这人口才蛮好的,水色暗自琢磨。转了个方向把他看了个真切。此人青灰衣色,缎料光鲜。浓眉粗长肿泡眼,蓄着腮帮胡须。水色一个寒颤,果然是人不可貌相。
那人又说:“你们不知道,万花楼被封当日。爷可就在红儿姑娘房里呢!嘿嘿!那妞儿的长得水嫩水嫩的,啧啧……”
“这位爷您说笑了吧,那天红儿姑娘不在楼子里吧,听说是被白净重金请出楼了。”
腮帮男脸上有些挂不住,眼见被戳穿也就讪讪一笑,喝了口茶把他那略显肥胖的身子缩了回去。水色在楼上捂着嘴,暗自好笑。
只是那人静坐了一会儿,又开始不安份了,“哎,你们说这里倒底是花楼还是茶楼?”
他这话一出,刚才都散了的人又围了上来,“那这位爷您说说!”
“那还用说吗,有姑娘的在这里当然是花楼了。”
“不对!秋掌柜的说这收楼的夫人是正经人,是茶楼才对!”
“花楼!”
“茶楼!”
不知为何,下面居然开始聚众成团了。争吵之声哗然宣起,一时之间居然惊动了水榭,琴声有停滞,舞步也开始凌乱起来。水色皱起眉,正犹豫着要不要出面。
“哎哟,各位爷在争执什么呢?”来人绿丫。她刚才去了后院,阿寺说前面有人捣乱,连忙赶了出来。
“你是何人啊?”腮帮男抬眼一看是个小丫头,神色多有鄙夷。
绿丫笑眯眯地接话:“哟,这不南街的陈员外吗,您来捧场让我这楼子蓬荜生辉啊。”
“你是?”陈员外心惊,这小丫头何许人也,居然能识破他的身份。
“奴家是个楼子里管事的。方才看到各位这里挺热闹的,奴家爱凑热闹,哪位爷说来听听。”
水色坐在楼上摸了鼻子,倾斜着大半身子静待下文。只见绿丫丝帕一甩,一个媚眼抛了出去。
倒塌!水色摸着臀部慢慢爬起来,默默的将翻倒在地上瓜子儿一粒粒捡起来装盘放好。眼见杂闹声渐渐消下去,水榭之上又恢复如初。楼下一票人围上绿丫问东问西起来。水色未再多留,她记得这陈员外跟絮语是有纠葛的。
“如此说来,絮语姑娘觉得应该怎么做!”
“夫人放心,絮语既然已经被撵了出来,断然没有再回头的理。”
“可是,若是那陈员外跟从前一样硬抢呢?”
方才水色寻着絮语的屋子找了进来,陈员外就在楼下。眼下弄不清楚他的目的是什么,但是他既然已经出现在这里了,那么不管他是不是知道絮语在此,都是个不可避免的麻烦。
絮语咬紧唇,虽是黯然神伤却未哭也未示弱,“夫人放心,絮语不会连累未名居的。”
水色赞许地笑了笑,“你且安心,签下合约你就是未名居的一份子。我怎么会把你往风口上推,我只是来提醒你见到他时莫要惊慌。白天你就不要出去了,有红儿姑娘压场就好。晚上你掩着面坐在后排,抚琴好了,莫要出声。待我先弄清楚他的意图。”
“多谢夫人!”絮语屏息凝神听了这些话,多有感激之情,她起身莲步微移。在水色面前站定,就要跪下去。
水色手快抓住她,“举手之劳不足以挂齿。絮语姑娘既已心定,又有何惧本是他们理亏在先,强抢我未名居的人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