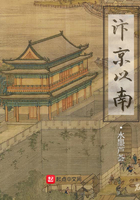张希
一想到那天我们见面时的情景,我就特别开心。那天,我们喊啊、笑啊,抱啊,疯啊,全然没有了年届半百中年妇女的庄重,仿佛还是30年前姑娘的活泼劲。
思绪回到了30年前。看,我们当年在钻塔边的合影,个个都是英姿飒爽,神采奕奕。不过,可千万别小看了我们这批“娇娇女”,钻机上的活儿我们全都要干。茫茫的旷野我们要入,湍急的河水我们要趟,入云的钻塔我们要爬,就连那些大件的机械我们也要自己扛。特定的环境造就了我们这批肯吃苦、敢拼搏的“铁”姑娘。下钻、起钻、搬家,取岩芯、量进尺、做记录,这些职业术语和这里边发生的故事,现在想起来依然是那么熟悉,那么自然,仿佛就在昨天。
说起钻塔,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搬家。十几米高的钻塔,每搬一次家,我们就得爬上塔顶去拆塔布,搬到新的钻点还得再上去缝一次。刚开始,我们也害怕,也不敢上,可怕也得上。我每次爬上去都只敢看上面,不敢看下面,因为越看下面,越不敢往上。越往上,风越大,呼啦啦地刮着脸庞。钻塔边上挂着的几块小铁皮也被敲得铛铛作响,敲得你腿脚发软、心尖打战,但慢慢的我们也就习惯了。
那时,我们女子钻机班的名字就叫“三八”女子争气钻,意思就是要给女同志争口气,要有“女子能顶半边天”的英雄气概,男同志能做的事,我们女同志照样能做。像抬水泵、取钻杆、搬枕木、处理钻机事故,等等,很多活儿我们都是自己干,并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工作中,为了节省体力,我们还发挥聪明才智,常常利用巧劲来干活。就说搬钻杆吧,开始,我们用管钳撬动钻杆,一点一点移动,十分费劲,一天干下来,累得够呛。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发现只要事先在机台板上垫一块厚一点长一点的铁皮,再把钻杆放在上面,利用钻杆与铁皮之间很小的摩擦力,我们只要轻轻一堆,钻杆就能很容易地从这一头滚到那一头了。发现这个小窍门的时候,我们别提多高兴了。
当然,我们也不是没遇到困难。那时,我们四班三运转作业,最担心的就是夜里钻机出故障。有一次,不巧让我和牛秀兰给赶上了。我俩捣鼓了半天,也没弄明白故障出在哪里,只好回工区驻地去请救兵。
我们的钻塔架在弋阳县境内一个叫林坂的地方,离工区驻地还有四、五里的山路,中途要穿过一片坟地。因为害怕,所以我俩决定一起回去找机长。那天晚上在回去的路上着实把我吓得不轻,当时已是夜里12点了,钻塔外,黑漆漆的一片,山风吹得树枝呼呼作响,怪吓人的。一路上,我们谁也不说话,脚下的步伐一点也不敢放慢,心里只盼着能快点到。要过坟地了,我俩紧张得心都要跳出来了,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壮着胆穿过了坟地,风一吹,背上有些凉,这才发觉自己已经出了一身冷汗。
我正想着和身边的牛秀兰说两句话时,她倒是先开了口,紧张兮兮地说:“你听,这是什么声音?”我立马停住脚步,凝神听起来。只听见两边的稻草在微风下摇摆声,没听出什么异样的声音。还没走两步,她又轻轻地说:“不对,是有声音。”我站在路边,再次凝神细听,耳边似乎真的有一种怪异的声音。这下,可把我俩吓着了。是什么声音,野兽?鬼?嗖嗖,嗖嗖,嗖嗖,这声音好像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我俩的呼吸也越来越急促。几乎又是同时,我们一起尖叫起来。真的有个东西从我们身边窜过去了。哎呀,原来是一条狗!
我们钻机班里的女钻工个个都很能干,手脚麻利,胆大心细。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班班长李秀云。她长得人高马大,是从河南农村过来的,特别能吃苦,也是钻机上公认的老实人,干活从来都不惜力气,有多大劲就使多大劲。当时,我们用管钳卸钻杆,机台板上一般得站两三个人才能踩得动,而她一个人就能卸得动。机长只要看见她在上面,就特别放心。有一年,她怀孕都好几个月了,居然还坚持上钻机工作,大家都为此惊叹不已。她工作时的那股认真劲,我们永远都记得。后来,女子钻机班撤销了,大家也都各奔东西,李秀云也跟着爱人定居上海了。
那时候的生活,虽然又苦又累,但是大家都很开心。下班后,我们常常在一起打球。工作中,谁家要是遇到什么事,其他的同事都会主动要求顶班,团结友爱、互相帮忙的气氛特别好。我在那里交了不少好朋友,现在想起这些,那时所经历的一切真是太有意思了。
(本文根据二六五大队退休职工张琪兰口述和李楠琦同志回忆文章整理)
编辑补白:20世纪70年代,二六五大队先后成立了“三八”女子找矿班和“三八”女子争气钻,前后共有六、七年的时间。虽然时间不长,但她们的存在、她们的业绩、以及她们为核地质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却是二六五大队铀矿勘查史上的一个精彩篇章。她们与男同志一样,以深山为家,与钻机做伴,为祖国的铀矿地质事业默默地做着奉献。据记载,二六五大队“三八”女子找矿班累计完成的找矿普查面积近4200平方公里,“三八”女子争气钻累计完成钻探工作量近270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