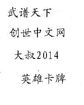音乐停止的时候陈小新还听到依依开心的笑声,她对所有的听众朋友说爱和不爱都是双方的权力,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依依并不是一个冷血动物,依依也会有自己的痛苦与快乐,但依依不愿意去做锦上添花或者说安眠药,依依给你的是一把盐,虽然当时疼,但对你的伤可以起到快速愈合的作用。好了,我们来接听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拨通我们的电话,请问你要说什么呢?
电话里是一个男人粗重的喘息声。
依依说这位朋友,请说话好吗?
男人说我操你妈!
男人的这句粗话骂得太快太突然,以至让依依好一阵子没有反应过来。陈小新不知道此时的依依是什么反应,但从那突然响起的音乐他就感觉到了。依依放的是那种杂乱无章又很狂暴的音乐,听起来好像有好几面破锣在敲。
酒桌上摆了几个小菜,桌子下面有暖和的火炉。两个扎着辫子红着脸蛋的女孩子在周围走来走去,她们操着东城的本地方言,一个上菜一个倒酒。
这个地方陈小新从来没有来过,如果不是依依,他也找不到这个地方。他们坐了近三个小时的的士,那的士随着依依的指挥从这个胡同里出来再拐到那个胡同去,转了几个胡同陈小新也记不清楚了。东城这破地方就是胡同多,一个连着一个,有点像北京的四合院。
他们来的这一家酒店是一家奇怪的酒店,这儿的菜千奇百怪,这儿的价格也是千奇百怪,从1000多一根的老黄瓜到1块钱1公斤的九节虾。
好像老板是一个疯子,他不按照市场的常规来叫价,而是任着心意想要多少就要多少。
这么一个四面漏风的破地方,每天只经营三桌,酒店的名字好像就叫三桌饭。无论你是多大的官,无论你有多少的钱,老板从来不破自己的规矩。听依依意思,她给这家的老板做了一期节目,然后排了一个多星期,老板才为他们腾出一张桌子。
陈小新不是第一次与依依吃饭了,他俩以前没有事的时候经常在一起吃饭,他们不仅在一起吃饭,还在一起逛街。有时候他们还去打打羽毛球。场子是依依家里的小区,那地方有一个专门打羽毛球的场子。依依的羽毛球打得比陈小新好多了,每次打球的时候他只有捡球的分儿。
依依感冒了,她穿着厚厚的羽绒服,脖子上还套着一条厚厚的马海毛围巾。她说一句话就咳嗽一声。陈小新想依依不应该来这个地方喝酒的,感冒了应该坐在家里喝点姜汤然后睡上一觉。
依依点了四个菜,那些菜都有着非常奇怪的名字,反正服务小姐说的是东城方言,陈小新也听不懂。他端起老板特制的免费的米酒,一杯又一杯地与依依碰撞。
这米酒虽然是特制的,但后劲特别大,喝过之后他们的脸上都已经像红透的苹果了。依依好像挺能喝的样子,虽然他俩经常在一起吃饭,但酒却是头一次喝。陈小新拿不准她能喝多少酒,就夺过她的酒杯说,不要喝了,依依,我们还是说说话吧?
你以为我会喝醉么?陈小新,你错了,我是我们电台里面最能喝酒的主持人。依依得意地向他挤了挤眼睛。
为什么要喝酒呢?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女孩子不要喝这么多酒,当然男人是没有办法。陈小新说。
心事?哈哈?我没有。陈小新,你有吗?今天有酒今天醉,来,干一杯。
依依来夺陈小新的酒杯。
他们的手在争夺中碰到了一起,依依的手冰冰的,像刚从冰箱里捞出来一样。陈小新的手因为碰到了依依的手,本能地抖动了一下缩了回来。
感觉有些麻麻的。
依依说我不想做了。
为什么?
没有意思。
是不是因为上次那个男人?
不是,陈小新,像这种事真的是太多了,刚主持节目那阵不仅有人骂啊还有人威胁我呢。
不会吧?他们为什么恨你?
因为我的语言击中了他们的弱点。人嘛,都是这个样子,虽然明知道自己是脆弱的,明知道别人的好话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但他们还是愿意听好话。而我说的正是他们不愿意听的,虽然心里承认是对的,但他们却不愿意听,尤其在电波里面,因为我打击了他们的自尊。陈小新,人就这么回事,如果自己钻了牛角尖,一般的人是无法把这个人拉回来的,除非他自己能够回头。
那个男人是谁你知道吗?真想揍他一顿,我当时都快气疯了,这种男人怎么能这样子呢?你们做主持的也不容易,表面上看着风光,其实难着呢。
你才知道啊?你知道我们新闻部的记者为什么被人绑架吗?原因就是因为他说了实话,得罪了一些人。我办这个栏目并没有别的意思,就希望自己做一枚指南针,让那些痛苦的人重新面对自己。现在我发现错了。
要不你调一个栏目吧?你毕竟在电台呆了这么久。
调哪儿去?其实,陈小新,告诉你吧,这不是我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这个栏目从这个周三就停播了。
真的?为什么?
能为什么呢?停了栏目,我也就不会在电台做了。做了好几年,够了,累了,倦了。陈小新,来,我们喝酒,酒逢知己千杯少啊,难得你能坐下来听我说话,难得我能把自己的心里话说给你听。我做节目做了快三年的时间了吧?总是听别人的,别人的快乐与痛苦,我却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的。你知道我也是一个普通人,也会有自己的快乐与不快乐,但我从来没有说过。
谢谢,有些事给朋友说说也许好受一点。
那你呢?陈小新,你会不会把心里话给别人说呢?依依突然把目光转向了陈小新。
陈小新想不会,虽然他心里一百个想说,但他知道自己不会说出来的。比如依依,陈小新不说给她听的原因是因为害怕,他害怕她听到后会为自己曾经的辉煌与现在的落魄感叹,然后再涌出无数个的为什么来。
他已经解释够了!
依依沉默了一阵子说我想开鲜花店,你知道这是我的梦想,我想坐在一间开满鲜花的屋子里,看着那些鲜花,看着它们的色;闻着它们的香,尤其来我花店的人们一定是最有爱心的,没有爱心的人是不会到鲜花店来的。
陈小新说很好啊,以后你就是鲜花店的老板啦,我为你打工怎么样?
依依说我们俩合伙怎么样?
陈小新喝了一口酒说,行,听你的。
那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布娃娃,像吊死鬼一样在陈小新的眼睛里摇晃。
那个布娃娃已经很破了,左边的手和右边的脚已经被水洗得发白了,胸前的那个小铃铛被风吹得发出呜呜拉拉的声音。陈小新起初看到它的时候吓了一跳,他还以为是谁家的孩子吊到了阳台上,后来他推开窗子才发现是一个破烂的布娃娃。
那个布娃娃和三岁多的孩子一般高大,那如皮肤一样的小手和小腿让陈小新不止一次地想到儿子。他已经习惯每天晚上都要看看那个吊在窗子外的布娃娃,让自己一边看布娃娃一边想象儿子的模样儿。
陈小新的钱包里有一张儿子五岁时的照片,他坐在家中的地毯上,手里拿着一支玩具枪,右眼眯着,左腿跪着,胖乎乎的小手扣动扳机,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镜头。
那个时候的他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身上的衣服全是从国外带来的牌子,那种丑宝宝的一套服装是东城人一个月的平均收入。
现在儿子长高了吧?他过得幸福吗?不知道妻子是不是还会给他买丑宝宝的衣服。还有他会不会恨自己?会不会想到自己呢?
陈小新坐在那儿想儿子,他很想很想给他打个电话,很想很想听听他的声音。可是陈小新不敢,他记得刚出来的时候打过一次电话,但儿子已经忘记了他的声音。话筒里面一个稚嫩的声音问陈小新找谁?后来那个声音就尖叫起来妈妈妈妈,他说他是爸爸。
不是你爸爸,你爸爸已经死了!陈小新的耳朵被这一句冰冷的怨恨的回答所击倒,手一软电话就摔到了地上。
厨房里还有几瓶啤酒,陈小新拧了好几圈啤酒盖子仍然紧紧地扣在那儿,他心里一急,两只手一用力啤酒瓶子就在两掌之间碎开了。随着清香的酒味还有迸出来的鲜血。
那些血跟在陈小新后面淌,从阳台到厨房,后来又跟到了卧室里。他感觉不到痛,虽然两只手血淋淋的。
陈小新觉得人有时候很奇怪,比如在依依没有告诉自己她要结婚之前,他一点儿也感觉不到自己在乎她。当他知道她要结婚了的消息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痛苦,心酸,失落。
在陈小新去咖啡厅等依依之前,他的心情还是非常激动非常兴奋的。
陈小新去楼下的理发店洗了洗头发,然后又让小姐刮了刮胡子。他的胡子已经很长了,头发也乱的像个鸡窝一样。
他们去的地方还是那家老咖啡屋,陈小新走进去发现这儿的服务员已经换光了,那些熟悉的面孔一个也没有了。
咖啡厅还是原来的那家咖啡厅,却找不到原来的人了。
依依的长发已经剪了,剪成了很短的发型。陈小新叫不出来这种发型的名字,但他知道东城最近很流行这种头。
依依笑嘻嘻地说这叫板刷。漂亮吗?她站起来,像模特儿那样在陈小新面前拧了好几圈子,然后她突然收起笑意说,陈小新,我今天叫你过来,有非常重要的事情给你说。
陈小新被她的庄重给吓住了,他在心里胡乱地猜测她会告诉自己什么,当他听她说要结婚了的时候,陈小新还是“腾”的一下子站了起来,他在激动的时候竟然冒出一句很傻瓜的话来:你和谁结婚?为什么要结婚?
你这个傻瓜,你说我和谁结婚?你说我为什么要结婚?依依突然间笑了起来。
陈小新说那是谁呢?
依依想了想说你不认识。
陈小新酸酸地说,恭喜你啊?没想到你这么快就结婚了。
再不结婚就真的嫁不出去了,女人不经老啊,依依沧桑地说。
他对你一定很好吧?陈小新问。
你说呢?两个人过日子哪有谈恋爱浪漫啊。依依摇了一下头。
那你爱他吗?陈小新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问,但这句话他不说出来心里堵得难受。
当然。这是一句陈小新早已经想到却不愿意接受的话。
那么,他爱你吗?陈小新仍然穷追不舍。
依依说你说呢?你会和一个不爱的人结婚吗?
陈小新说那要看情况。有时候结婚并不一定是为了爱情,有时候不结婚也并不代表不爱。比如像前几年分房末班车的时候,多少夫妻只是为了一套房子而草草地结婚了呢。陈小新怕依依不明白,就举例给她听。
我现在也不分房子,也不缺钱。怎么了?我结婚你不高兴啊?依依向陈小新挤了挤眼睛。
没,没有啊,我只是觉得有些突然而已。以前你好像没有提过他。陈小新极力掩饰自己的失态。
你不知道并不代表没有嘛,看你这么聪明的人也犯傻了。你最近的生活有什么改变没有?依依说。
陈小新叹息了一声说,能有什么改变呢?还是老样子。你呢?
在搞鲜花店的事啊,等到我把头绪理出来,你可要出来做事了,要不然我自己就会累死。依依笑嘻嘻地说。
嫁了一个有钱的老公还这么辛苦干嘛?陈小新刺激她。
他有钱不关我的事,陈小新,你知道我不靠男人生活的。
行,改天叫他一起过来吃饭吧?
谁啊?依依明知故问。
你说呢?你们都要结婚了还不带给我见见?太过分了吧?再说了婚姻大事可不能太着急,万一有一天你发现他不适合你了怎么办呢?
咦,怎么这么多醋啊?酸死了。依依故意把鼻子伸过来,在咖啡里闻着。
陈小新从来没有找过小姐,这是真的。
陈小新知道自己为什么不找小姐,也知道为什么总有一些男人喜欢找小姐。他们的安全意识与欣赏水平与他不是一个档次,而且他还知道小姐从某一方面代表着男人的能力与魅力。
陈小新起初只是想跟着邓爱国去唱唱歌,根本没有想到要去找小姐。
邓爱国说他哥们儿刚开了一个歌厅,所以他要去捧捧场。
要了房间后,邓爱国就忙着打电话约人,他一边打电话一边冲陈小新挤眼睛,他说今天晚上来的两个小姐绝对养眼。
服务生送了大号的果盘,然后又来了一打加十啤酒,这种啤酒是西城生产的,以前陈小新在西城的时候还和加十的老总吃了几次饭。陈小新与他吃饭的时候,加十啤酒还只能在西城销售,而现在加十啤酒已经风靡全国了。只要有酒的地方就有加十,只要有广告的地方就有加十广告。
想想真他妈的不公平,以前与他吃饭的时候陈小新还是一个什么都高于他的行业大哥,现在他知道这个坐在包房里,胡子拉碴的男人是谁啊。
邓爱国唱歌的水平真的不敢恭维,他不仅跑调而且嗓子嘶哑,一个高音调上不去的时候陈小新就听到了邓爱国的愤怒的阿阿声。陈小新坐在那儿,一边看邓爱国的笑话一边耐心地等待着佳人的到来。
陈小新以为邓爱国叫来的女孩子不是小姐,而且看她们的装扮也不像小姐,这两个女孩子也就是十七八的年龄,穿着很平常的衣服,坐在他们俩的身边,样子纯洁得像在校的女学生。
可是当邓爱国的手突然搂住那个女孩子的腰,当女孩子的头靠到陈小新的肩膀上,他就明白了。
包房里灯光阴暗,倩影成双。邓爱国那公鸭嗓一样的声音强奸着人们的耳朵,他一会儿男声一会儿女声地唱歌。陈小新实在受不了就和邓爱国玩剪子包袱,谁输了谁喝酒。
这样的夜晚与别的夜晚有什么不同呢?这样的包房与别的包房有什么不同呢?现在随便让我们推开一间包房,看看里面的情景吧,每一个包房里都有人,男人和女人,每一个包房里都有酒,啤酒和红酒,每一个包房里都有扯着嗓子表现唱歌的男人女人,只是唱得好与不好而已。
我们看到包房里因为喝了酒,而显得暧昧、热情、冲动起来。小姐们穿着短短的皮裙,长长的靴子,有的还在嘴边叼了一支烟,她们坐在男人的身边或者大腿上,发嗲、撒娇、轻笑,而男人因为有了佳人的相伴,而显得精神焕发,兴奋异常。邓爱国已经搂了其中一位小姐的腰,唱着酸得掉牙的情歌:等到太阳落了西山头,让你亲个够……包房里的对话虽不精彩,但却像毒瘾一样从这个角落传染到那个角落。那个叫邓爱国和陈小新的男人,他们一人搂了一个女人,坐在包房里热情万分地唱歌,喝酒,然后说着自己都不知道的谎话。
老板是哪儿人啊?
黄城,就是黄色的黄。
老乡呢,我家住在离黄城不远的地方。
真的啊?
真的,不骗老乡。来,老乡,我们干一杯吧,不是说了么,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么。
你的口音不像黄城人呢?
来东城时间久了,就入乡随俗了。
老板在哪儿高就啊?
打工啊,和你们一样。
不会的,一看老板就不是打工的,看看这像弹琴一样的手,怕是动动脑子就挣钱的吧?来来,我给老板看看手相。
看什么手相啊?是不是看看今年有没有桃花运啊?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没有女朋友呢?
老板真没有女朋友啊?像你这么帅的男人怎么会没有女朋友呢?怕是多得数不过来了吧?
真的没有啊,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陈小新听到邓爱国一边握着小姐的腰一边厚着脸皮说。
老板,不要开玩笑啦,我会当真的。老板!小姐好像只会这个称呼,来的人不管是不是真的有钱真的是老板,小姐都会叫他们老板,然后再按照老板的喜好说一些动听的话,唱唱歌,跳跳舞。
看邓爱国又搂又亲的样子,他以为这一切都可以免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