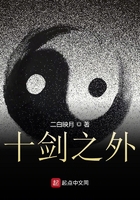关于“古文运动”所谓“古文”,是针对“时文”即魏晋以来形成、至初盛唐仍旧流行的骈体文而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先秦两汉时单行散句、没有规定形式的文体。但韩愈他们提倡古文,虽也包含文体变革的要求,其根本的目标却并不在文体上。
文的骈俪化与诗的格律化同是六朝文学的结晶和主要特征。尤其骈文的兴盛,对于提出“文”、“笔”之分,区别文学与非文学有重要的意义。但骈文的兴盛也带来一系列不同性质的问题:一是骈文的写作过度膨胀,被推进到各种实用文的领域,使得后者的实用功能受到削弱;二是从文学性散文来看,由于骈文的形式要求越来越严格,对偶、藻饰、用典、声律都成为其必备的要素,给大多数作者自由地抒写思想感情造成了困难。这种情况从盛唐时期开始发生了较明显的改变,在一些作者笔下,实用性散文如奏疏、论说、书札等在形式上已经逐渐变得松动,文学性散文也趋向轻快自由,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简单地说,如果单纯从实用功能或审美功能出发看问题,在骈文高度兴盛以后,文章再度由骈人散、骈散结合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也并不存在骄、散的截然对立。但骄文兴盛的现象还具有另外一层意义,即它对形式的讲究和唯美倾向,隔断了以政治、教化功用为根本目标的儒家文学观对文学的支配,同时,这种现象也正反映着魏晋以来儒学独尊地位的失落。而提倡“古文”者之所以对骈文提出严厉的批判,主要的原因也在于此。
但“古文”的复兴,还有赖于韩愈的出现。这一方面是因为到了韩愈活动的年代,文章由骈入散的趋势更加明显了,另一方面则因为韩愈比他的前辈们更擅长于散文的写作,他的身边又聚集了不少同道之人,具有更大的号召力。柳宗元虽然并不属于韩愈那个作家群体,而且由于他长期贬谪在南方,离当时的文学中心较远,在当时的实际影响没有韩愈那么大,但他的古文理论与韩愈是一致的,彼此间有一种相互呼应的作用。
韩愈、柳宗元的散文韩愈的《原道》、《原性》、《论佛骨表》、《师说》等说理文过去很受一般古文家的称赏,但并不属文学性的作品。另有一些以议论为中心的短文,如《送孟东野序》、《送董邵南序》、《送李愿归盘谷序》等,由于文中包含着对友人的同情与慰解,发泄了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不平之气,有较多的感情色彩,写得颇有动人之处。此外,还有一些近乎寓言的杂感,借生动的形象抒写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或穷愁寂寞的叹息,情绪更显得尖锐,如著名的《说马》: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在韩愈的散文中,悼念其侄韩老成的《祭十二郎文》尤其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哀吊之文前人多用骈体或四言韵文写作,在整齐的格式中求得一种庄肃之感。而此文全无格式、套语,而且不像韩愈其他文章那样讲究结构。全文以向死者诉说的口吻写成,哀家族之凋落,哀自身之未老先衰,哀死者之早天,疑天理疑神明,疑生死之数乃至疑后嗣之成立,极写内心之辛酸悲恸。中间一段写初闻噩耗时将信将疑、不甘相信又不得不信的心理,真实而动人;结末一节叹生死永别,尤其哀切:
呜呼!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得抚汝以尽哀。敛不凭其棺,窆不临其穴。吾行负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与汝相养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吾实为之,其又何尤。彼苍者天,曷其有极!
这一段文字中其实也包含不少对偶的成分。但这种对偶跟情绪的波动非常密合,显得相当自然,不同于一般骈文所追求的精致与紧密。从全文来看,语意反复而一气贯注,体现了在特定情景下散体文相对于骈体文的优长。而把韩文上述几种类型加以比较,又可以看出大体愈是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脱离“明道”原则愈远,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古文运动核心理论对文学的束缚。
韩愈还写过一些诙谐性的或带有游戏色彩的散文,当时人裴度就说他“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寄李翱书》),这也反映了韩愈个性活跃和富于想象力的一面。这类文章有《毛颖传》、《鳄鱼文》、《石鼎联句诗序》、《送穷文》等,其优劣高下大抵取决于作者人生感受、生活情感投人的深浅。如《石鼎联旬诗序》以一种近乎小说的情节描述道士轩辕弥明与刘师服、侯喜二人联诗的戏剧性过程,把两个文人酸文假醋的模样、前倔后恭的心理和道士不拘小节、放荡机智的形象写得十分生动,这里面显然包含着韩愈对诗的自得之情。《送穷文》则虚设“主人”具柳车草船送“穷鬼”离去反被穷鬼和他的朋辈教训了一番的情节,对自己久来陷于穷困而难于自拔的遭遇加以嘲戏,以一种幽默的态度求得心理压力的释放。文章开头是主人致穷鬼的庄肃的送别辞,结束处却是五鬼以滑稽的腔调说出一番堂皇的大道理,在荒唐悠谬中显出无奈的心清。兹录最后一小节:
言未毕,五鬼相与张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顿脚,失笑相顾,徐谓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为,驱我令去,小黠大痴。人生一世,其大几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于时,乃与天通。携持琬琰,易一羊皮;饮于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谁过于予?虽遭斥逐,不忍子疏。谓予不信,请质《诗》。”主人于是垂头丧气,上手称谢,烧车与船,延之上座。
中国古代诙谐幽默之文不多,这种生动有趣的文章在文学史上是应有一席之地的。
柳宗元散文的情况也与韩愈相类。在其全部作品中,文学性散文占的比例不大;而且一般来说,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大抵并不体现“明道”的作用。这种性质的散文主要有两类:寓言和山水游记。寓言如著名的《蝜蝂传》借小虫讽刺那些“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不知死之将至的贪心者;《三戒·黔之驴》则借驴比喻那些外强中干、实无所能的庞然大物,想象丰富,语言犀利,篇幅虽短而寓意深刻。但柳宗元散文中写得最好的是山水游记。
散文中描摹山水的内容自六朝以来就很兴盛,一些名家的书信差不多就是写山水的小品,郦道元《水经注》中更保留了许多精彩的片断。但山水游记成为一种单独的文章类型,则是从柳宗元才开始的。柳氏的这类散文大抵均作于他贬居西南边地时,游山玩水是他孤寂生活中的精神寄托。所以他并不是单纯地描摹景物,而是将感情投射于自然,通过对山水的描写呈现自己的心境。像《钻鉧潭西小丘记》所说其处“清冷之状与图谋,瀴瀴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正是一种物我合一的境界。因而,他笔下的山水总是体现出人格化的孤洁清雅、凄清幽怨的情调。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王鼠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蹀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天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写景部分喜用短句,像《袁家渴记》写风,“振动大木,掩再众草,纷红骇绿,蓊勃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飏葳蕤,与时推移”,连用八个四字句,明显是保留了辞赋与骈文的特点。
晚唐散文晚唐后期伴随着诗教说的再度兴起,散文领域内类似“文以明道”的主张也再度被提出。如皮日休写过《请韩文公配享太学书》,要求将韩愈配享于孔子庙堂,在《皮子文薮·序》中又自称他的各种文章“皆上剥远非,下补近失,非空言也”,显然以继承韩愈的事业为己任。但在晚唐后期的乱世中,这种主张显得非常无力,持这种主张的人也写不出韩、柳那样的尚有自信因而也还有气势的“明道”文章。倒是他们在失望与愤慨之下写出的一些讽刺性的短文,还略有特色。这类文章的作者除皮日休外,尚有罗隐、陆龟蒙等。
这种讽刺性的短文篇制非常短小,通常仅二三百字,也有数十字的,所以从文章形态来看是相当新颖的,对宋元以降的短文有开启先河的作用。不过皮日休、陆龟蒙所作实过于切露且议论太盛,并没有真正发掘出短文可能具有的优长。罗隐所作则强于前二人,盖缘少作基于儒家道统而不宜于短文的宏大议论。如其集中列为赋类《秋虫吟》连序在内也仅有数十字:
秋虫,蜘蛛也,致身罗网间,实腹亦罗网间。愚感其理有得丧,因以言赋之曰:物之小兮,迎网而毙,物之大兮,兼网而逝。而网也者,绳其小而不绳其大,吾不知尔身之危兮,腹之馁兮,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