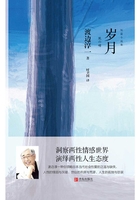按照我的推测,这群羊的来历应该是这样的:有这么个羊倌,要么是个孩子,要么是个老人,在高速路边的荒地里放羊。羊吃饱了,羊倌的觉睡足了,他们就打算横穿高速公路回家。他们的家也许就在附近的村庄,因为这条路车辆稀少,他们已经习惯把它当成了一条没有任何危险和意外的乡间小路。
死掉的是只小羊羔。它的一条腿被轮胎压住,没有流血,但是它连一点挣扎的意识都没有,在我看来,这只小绵羊像是团洁白柔软的棉花被人塞到车轮下。它甚至没有发出“咩咩”的声音。它已经不会叫了。另外两只绵羊,一只被撞出三四米,一只撞出七八米。那只稍远些的正试图着站起来,连续站了四五次,每次都瘫在那儿。
我们都围住了稍近的那只。我们都围住它是因为它浑身是血。
怎么会这样?王小花说,怎么会这样呢?你喝酒了就不能开慢一点吗?
我开得不快,一点都不快,四哥点支烟说,死了就死了,我们走吧。是它违反了交通规则,又不是我们。你说是吧?他朝刘荣“嘿嘿”地笑了两声说,要是人的话就糟了。我觉得四哥真喝高了,我觉得他不该在这个时候将动物跟人进行比较。他或许已然忘记了前几天刘荣工厂发生的事。刘荣只是低头,用粗糙的手指小心拨弄着那只羊的犄角,间或翻翻羊的眼皮。我从未在阳光下看一双将死的动物眼睛。它眼睛黑圆硕大,仿佛随时会从眼眶中滚出。
它流泪了,刘荣说,它竟然流泪了。刘荣的声音有点颤抖,他说,原来羊也会哭啊……
它真的哭了,王小花喃喃着说,它一定很疼。她说这话时似乎感受到了羊的抽搐,她的身体象征性地哆嗦了下,然后她试图去抚摸羊的嘴巴,当她的手即将触摸到时,却迫不及待地抽回。她果敢地从书包里掏出条手绢,将手指一根根擦了个遍。当她站立起来时,她这才发觉她的长筒丝袜怎么就染了血迹,她夸张地尖叫一声,一把抓住四哥的胳膊。我看到她耳朵上的肉瘤有节奏地跳着。她是真怕了。
我们别在这里耽搁时间了,四哥说,我们走吧,我们还要去看李红旗呢。周建歧呢?他嘟囔声,周建歧呢?我们走吧。大家上车!我说周建歧在做祈祷,也许在做法事,我们等会儿吧。四哥狐疑地环顾着四周。他太不了解周建歧了。他看到周建歧跪在马路边时突然放声大笑,他在干什么?四哥问,他不会真有毛病吧?我说他没毛病,他是佛家弟子,他正在超度那只死掉的小羊羔。
周建歧的样子很虔诚,现在虔诚的人越来越稀有,我对他跪在那里一点都不感到滑稽或者突兀。前几天我们去刘荣家,我们去刘荣家是因为刘荣家出了点事:他家的一个雇佣工人,由于违规操作被电死了。我们去安慰刘荣老婆。他老婆是个心地良善的女人,他们给了死者家属八万块钱抚恤金,但他老婆仍夜夜做噩梦。就是在刘荣家,我第一次看到周建歧做法事。也许称不上法事,他的仪式简单明了,缺少一场正规法事应有的肃穆和繁琐。他只是在刘荣家的院子里,朝东南西北各磕一个响头,然后跪在那儿,撅着肥硕的屁股,弯着他永远直不起来的水蛇腰念念有词。我们都不敢上前阻止他。他一直在那里跪了十分钟,后来他从容地站起来,对面色苍白的女人说,你们家那个整天哭的鬼,已经被我劝走了,他再也不会来了,他已经被我的佛语送到天堂了。
而现在,周建歧的举动让四哥厌烦起来,他对我们喊,不就是几只羊吗?不就是几只羊吗?大不了陪放羊的几块钱,至于这样吗?你!他指着跪在路边的周建歧说,给我站起来!你!他又指着蹲在那里观察绵羊的刘荣说,给我站起来!他迅速地瞥我一眼,我只好笑笑。他继续嚷道,我他妈推了正经事,陪你们去看李红旗,你们却在这里穷酸磨唧,真不是东西啊!他话音未落手机就响了。他迅捷地将手机放至耳边,对着手机吵,孩子哭了就给他喂点蜂蜜!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蜂蜜在哪儿?蜂蜜就在冰箱里!没了?没了就去买啊!又不是没长腿!
他颇为气愤地关掉手机。他满脸通红。他本来是个个子高大、斯文有礼、思路清晰的商人,但他似乎确实对周遭人的行经感到愤怒。当然,他的愤怒并不能影响什么,周建歧仍跪着,刘荣仍蹲着,只有我跟王小花,颇为恐慌地盯住他。他叹息声,皱皱眉头,说,我……我没喝多。你们别那样看我。
也许吧,他没喝多,喝多的是刘荣。他从绵羊身边站起来,直接奔向周建歧,然后他抬起右腿,朝周建歧的腰身猛地踹了一脚。在去看李红旗的半路上,在初春无聊的下午,我们看到周建歧在刘荣腿下倒了下去,他动作缓慢,有点像一个心生胆怯的学生在老师的胁迫下做了半个东倒西歪、颇为勉强的一跃前滚翻:周建歧的身体最后被高速护栏卡住,头朝下腿朝上,倒立的眼睛死鱼样绝望地望着我们,而他的双手依然保持着合十祈祷的姿势,另外,他皮鞋带没系紧,所以在猥亵着捅向天空的两只脚中,一只穿着皮鞋,另外一只穿着袜子。刘荣踹完之后后退几步,呆掉,仿佛不清楚自己刚才做了些什么。在众目睽睽下,周建歧艰难地又做了半个前滚翻,这样,他双脚重新回归土地时的姿态是这样的:他背对我们而跪,跟事发前他跪在那里祈祷时一样从容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