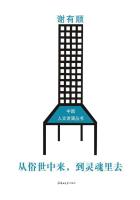我努力地排遣自己,思索着这次来的目的和计划,我一定要好好休养,而且按着自己规定的时间去生活。于是我又回到房子里来了,既然不能睡,而写笔记又是多么无聊呵!
幸好不久刘二妈来看我了,她一进来,那小姑娘跟着也来了,后来那媳妇也来了。她们都坐到我的炕上,围着一个小火盆。那小姑娘便察看着那小方炕桌上的我的用具。
“那时谁也顾不到谁,”刘二妈述说着一年半前鬼子打到霞村来的事,“咱们住在山上的还好点,跑得快,村底下的人家有好些都没有跑走,也是命定下的,早不早迟不迟,这天咱们家的贞贞却跑到天主堂去了,后来才知道她是找那个外国神父要做姑姑去的,为的也是风声不好,她爹正在替她讲亲事,是西柳村一家米铺的小老板,年纪快三十了,填房,家道厚实,咱们都说话,就只贞贞自己不愿意,她向着她爹哭过。别的事她爹都能依她,就只这件事老头子不让,咱们老大又没儿,总企望把女儿许个好人家。谁知道贞贞却赌气跑到天主堂去了,就那一忽儿,落在火坑了哪,您说做娘老子的怎不伤心……”
“哭的是她的娘么?”
“就是她娘。”
“你的侄女儿呢?”
“侄女儿么,到底是年轻人,昨天回来哭了一场,今天又欢天喜地到会上去了,才十八岁呢。”
“听说做过日本人太太,真的么?”
“这就难说了,咱也摸不清,谣言自然是多得很,病是已经弄上身了,到那种地方,还保得住干净么?小老板的那头亲事,还不吹了,谁还肯要鬼子用过的女人!的的确确是有病,昨天晚上她自己也说了。她这一跑,真变了,她说起鬼子来就像说到家常便饭似的,才十八岁呢,已经一点也不害臊了。”
“夏大宝今天还来过呢,娘!”那媳妇悄声地说着,用探问的眼睛望着二妈。
“夏大宝是谁呢?”
“是村底下磨房里的一个小伙计,早先小的时候同咱们贞贞同过一年学,两个要好得很,可是他家穷,连咱们家也不如,他正经也不敢怎样的,偏偏咱们贞贞痴心痴意,总要去缠着他,一来又怪了他。要去做姑姑也还不是为了他?自从贞贞给日本鬼子弄去后,他倒常来看看咱们老大两口子。起先咱们大爹一见他就气,有时骂他,他也不说什么,骂走了第二次又来,倒是一个有良心的孩子,现在自卫队当一个小排长呢。他今天又来了,好像向咱们大妈求亲来着呢,只听见她哭,后来他也哭着走了。”
“他知不知道你侄女儿的情形呢?”
“怎会不知道?这村子里就没有人不清楚,全比咱们自己还清楚呢。”
“娘,人都说夏大宝是个傻孩子呢。”
“思,这孩子总算有良心,咱是愿意这头亲事的。自从鬼子来后,谁还再是有钱的人呢?看老大两口子的口气,也是答应的。唉,要不是这孩子,谁肯来要呢?莫说有病,名声就实在够受了。”
“就是那个穿深蓝色短棉袄,戴一顶古铜色翻边毡帽的。”小姑娘闪着好奇的眼光,似乎也很了解这回事。
在我记忆里出现了这样一个人影:今天清晨我出外散步的时候,看见了这么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有着一副很机伶也很忠厚的面孔。他站在我们院子外边,却又并不打算走进来的样子;约莫当我回家时,又看他从后边的松林里走出来。我只以为是这院子里人或邻院的人,我那时并没有很注意他,现在想起来,倒觉得的确是一个短小精悍、很不坏的年轻人。
我的休养计划怕不能完成了,为什么我的思绪这样地乱?我并不着急于要见什么人,但我幻想中的故事是不断地增加着。
阿桂现出一副很明白我的神气,望着我笑了一下便走出去了。
我明白了她的意思,于是来回在炕上忙碌了一番,觉得我们的铺、灯、火都明亮了许多。我刚把茶缸子搁在火上的时候,果然阿桂已经回到门口了,我听见她后边还跟得有人。
“有客人来了,××同志!”阿桂还没有说完,便听见另外一个声音噗哧一笑:“嘻……”
在房门口我握住了这并不熟识的人的手了。她的手滚烫,使我不能不略微吃惊。她跟着阿桂爬上炕去时,在她的背上,长长地垂着一条发辫。
这间使我感到非常沉闷的窑洞,在这新来者的眼里,却很新鲜似的,她用满有兴致的眼光环绕地探视着。她身子稍稍向后仰地坐在我的对面,两手分开撑住她坐的铺盖上,并不打算说什么话似的,最后把眼光安详地落在我的脸上了。阴影把她的眼睛画得很长,下巴很尖。虽在很浓厚的阴影之下的眼睛,那眼珠却被灯光和火光照得很明亮,就像两扇在夏天的野外屋宇里洞开的窗子,是那么坦白,没有尘垢。
我也不知道如何来开始我们的谈话,怎么能不碰着她的伤口,不会损害到她的自尊心。我便先从缸子里倒了一杯已经热了的茶。
“你是南方人吧?我猜你是的,你不像咱们省里的人。”倒是贞贞先说了。
“你见过很多南方人么?”我想最好随她高兴说什么我就跟着说什么。
“不,”她摇着头,仍旧盯着我瞧,“我只见过几个,总是有些不同。我喜欢你们那里人,南方的女人都能念很多很多的书,不像咱们,我愿意跟你学,你教我好么?”
我答应她之后忽地她又说了:“日本的女人也都会念很多很多书,那些鬼子兵都藏得有几封写得漂亮的信:有的是他们的婆姨来的,有的是相好来的,也有不认识的姑娘们写信给他们,还夹上一张照片,写了好些肉麻的话,也不知道她们是不是真心,总哄得那些鬼子当宝贝似地揣在怀里。”
“听说你会说日本话,是么?”
在她脸上轻微地闪露了一下羞赧的颜色,接着又很坦然地说下去:“时间太久了,跑来跑去一年多,多少就会了一点儿,懂得他们说话很有用处。”
“你跟着他们跑了很多地方么?”
“不是老跟着一个队伍跑的,人家总以为我做了鬼子官太太,享富贵荣华,实际我跑回来过两次,连现在这回是第三次了。后来我是被派去的,也是没有办法,我在那里熟,工作重要,一时又找不到别的人。现在他们不再派我去了,要替我治病。也好,我也挂牵我的爹娘,回来看看他们。可是娘真没有办法,没有儿女是哭,有了儿女还是哭。”
“你一定吃了很多的苦吧。”
“她吃的苦真是想也想不到,”阿桂露出一副难受的样子,像要哭似的,“做了女人真倒霉,贞贞你再说吧。”她更挤拢去,紧靠她身边。
“苦么,”贞贞像回忆着一件辽远的事一样,“现在也说不清。有些是当时难受,于今想来也没有什么;有些是当时倒也马马虎虎地过去了,回想起来却实在伤心呢,一年多,日子也就过去了。这次一路回来,好些人都奇怪地望着我。就说这村子的人吧,都把我当一个外路人,有亲热我的,也有逃避我的。再说家里几个人吧,还不都一样,谁都偷偷地瞧我,没有人把我当原来的贞贞看了。我变了么,想来想去,我一点也没有变,要说,也就心变硬一点罢了。人在那种地方住过,不硬一点心肠还行么,也是因为没有办法,逼得那么做的哪!”
一点有病的样子也没有,她的脸色红润,声音清晰,不显得拘束,也不觉得粗野。她并不含一点夸张,也使人感觉不到她有什么牢骚,或是悲凉的意味,我忍不住要问到她的病了。
“人大约总是这样,哪怕到了更坏的地方,还不是只得这样,硬着头皮挺着腰肢过下去,难道死了不成?后来我同咱们自己人有了联系,就更不怕了。我看见日本鬼子吃败仗,游击队四处活动,人心一天天好起来,我想我吃点苦,也划得来,我总得找活路,还要活得有意思,除非万不得已。所以他们说要替我治病,我想也好,治了总好些。这几天病倒不觉得什么了。路过张家驿时,住了两天,他们替我打了两次药针,又给了一些药我吃。只有今年秋天的时候,那才厉害,人家说我肚子里面烂了,又赶上有一个消息要立刻送回来,找不到一个能代替的人,那晚上摸黑我一个人来回走了三十里,走一步,痛一步,只想坐着不走了。要是别的不关紧要的事,我一定不走回去了,可是这不行哪,唉,又怕被鬼子认出来,又怕误了时间,后来整整睡了一个星期,才又拖着起了身。一条命要死好像也不大容易,你说是么?”
她并没有等我的答复,却又继续说下去了。
有的时候,她停顿下来,在这时间,她也望望我们,也许是在我们脸上找点反应,也许她只是思索着别的。看得出阿桂比贞贞显得更难受,阿桂大半的时候沉默着,有时说几句话,她说的话总只为的传达出她的无限的同情,但她沉默时,却更显得她为贞贞的话所震慑住了,她的灵魂被压抑,她感受了贞贞过去所受的那些苦难。
我以为那说话的人丝毫没有想到要博得别人的同情,纵是别人正为她分担了那些罪过,她似乎也没有感觉到,同时也正因为如此,就使人觉得更可同情了。如果她说起她这段历史的时候,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心平气和,甚至使你以为她是在说旁人那样,那是宁肯听她哭一场,哪怕你自己也陪着她哭,都是觉得好受些的。
后来阿桂倒哭了,贞贞反来劝她。我本有许多话准备同贞贞说的,也说不出口了,我愿意保持住我的沉默。当她走后,我强制自己在灯下读了一个钟头的书,连睡得那么邻近的阿桂,也不看她一眼,或问她一句,哪怕她老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一声一声地叹息着。
以后贞贞每天都来我这里闲谈,她不只是说她自己,也常常很好奇地问我许多那些不属于她的生活中的事。有时我的话说得很远,她便显得很吃力地听着,却是非常要听的。我们也一同走到村底下去,年轻人都对她很好;自然都是那些活动分子。但像杂货店老板那一类的人,总是铁青着脸孔,冷冷地望着我们,他们嫌厌她,鄙视她,而且连我也当着不是同类的人的样子看待了。尤其那一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敌人强奸而骄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