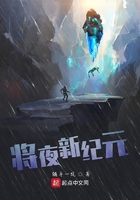我一把工会卡交给他们,这些艺术家便开始从各个角度打量这些工会卡。一个证件只是看起来像还不够,还要感觉正确。比如,来回翻折时的声音是怎样的?所以,你就要检查纸质,到纸张库存里找出同质的纸张。同样,还有身份证件的薄板压层。如果半夜有人拦住你,检查你的证件,他们可能根本看不清楚,但他们可以用手摸。也许为了防伪,某些证件摸起来会比较黏。这些都是绘图组在伪造证件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艾伦·杜勒斯说得最好:“任何一个合格的特工组织都应该可以制作对方的货币。”换句话说,每个国家都需要有无懈可击的安全措施,同时也要积极开展秘密工作,拆解、分析对手的安全手段,然后进行仿制。
整理完制片经理的文件袋后,下一步任务就是“客人”的过境文件。既然已经分配好身份,我们就要证明他们是从什么地方入境伊朗的,这样才好把他们带出来。
这个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并不容易。我们不仅要准备相关的预定机票,而且还要在“客人”的护照上盖上各种证件和过境印章,证明他们走的确实是我们所说的路线。这个过程通常十分复杂,需要几十个技术高超的官员密切协作。在这次行动中,我们决定让“客人”先周游世界,最后经香港飞往伊朗。这就意味着,乔需要到档案库,搜寻“客人”离开时香港移民局所使用的公章。在找到正确的印章之后,我需要把印章送给制作室。制作室负责监督印章能够在技术服务办公室内各个部门之间流通。等这一过程结束后,乔就会收到一个印有正确印章的旅行文件。但这只是一个国家的过境记录而已。设想一下,他们一共需要在每个旅行文件上盖几十个印章。另外,想象一下,同时进行的此类行动成百上千,这样你就知道在制图室工作的复杂性了。
就在制图部门全力以赴制作各种文件材料和仿制印章时,为了计划能够完整实施,伪装部门的多丽丝正忙着筹集一些伪装材料。这些材料将会被放进由渥太华寄给驻德黑兰大使馆的包裹里。
因为我即将飞往德黑兰,所以在工作上亲自参与的程度比平时要高一些,多丽丝时常带着进展报告来找我。因为“客人们”没有进行复杂伪装的经验,所以我们更强调让他们通过形象气质和行为举止的改变来伪装。外交官在外表上通常是偏保守的,因此我们要让他们变得更招摇、时尚和性感。身上多喷香水,多用剃须水,不系衬衣扣子,穿紧身裤,戴金链子和带响动的珠宝,用吹风机吹头发——总之就是用一些他们平时绝对不会用的材料。他们说话的时候要更大声,更粗鲁,更装腔作势,甚至有点傲慢。总之,就是要让外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们是在好莱坞混饭的。
我们不知道要寄的东西是否太多,因为我们的伪装材料要跟所有的文件放到同一个包裹。多丽丝给每位“客人”都准备了一个百宝箱,里面装着发胶、化妆品、黑框眼镜和眼线笔,等等。此外,里面还有一张打印出来的使用说明,指导“客人”改变自己的外表。工具箱里还放着西德尔为摄影师准备的取景器,还有我将要随身携带的剧本和素描垫等材料。
在总部和国务院仍在为各种伪装方案举棋不定时,我们写了一份更新版的行动计划,提议让我带着三份行动方案到伊朗。到达伊朗后,我会把这三份计划交给“客人”,让他们自己决定是单个逃离,还是整体逃离,也看看他们愿意采用哪种伪装方案。虽然这并不是最理想的结果,但是因为太多的政府部门插手这件事,我觉得这是我能够及时赶到德黑兰的唯一方法。我也知道,既然派我去向“客人们”传达这三种行动计划,我可以劝服他们按照我觉得正确的方案走。我知道加拿大人现在十分焦虑,是时候把我们的外交官带出来了,要不然就没有时间了。
从加州回来一个星期后,一切都准备就绪了。我和乔一起登上一架飞机,飞往渥太华准备包裹行李。
一到加拿大,我和乔开始准备最后的文件,搜集其他可以随身携带的小物件,诸如:枫叶胸针、纸板火柴、商务名片和收据——这次收拾的东西都能让“客人”看起来更像加拿大人。
加拿大外交包裹只有枕头套那么大,刚刚能装下我们的文件袋和伪装材料。加拿大的快递员显然比美国国务院的快递员轻松。美国国务院的快递员经常要搬运好几个邮包大的包裹。加拿大快递员只能带一个包裹,而且要随时都带在身边。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我们有些伪装材料不得不留下来。
在飞往加拿大之前,我曾检查了一遍伪装美国英文教师的所有材料,我已知道这有可能会造成一种尴尬的情况。加拿大人已经成功获得了证明“客人们”是加拿大人的身份的材料——驾照、加拿大医保卡、营养学家的商务名片——但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对中情局申请的证明“客人们”是英文教师的材料却推进缓慢。我记得在离开前一天下午7点到制图办公室询问杜鲁门他们都准备好什么了。他手里的东西只有一个大超市的信用卡。我觉得有点东西总比没有好,但是当我给技术服务办公室主任弗雷德·格拉乌斯打电话询问我们能不能用这张信用卡时,他的回答却是:“不能。”所以,为虚假美国身份筹备的文件材料远远比不上为假加拿大身份所准备的材料。实际上,我们之所以还要把假美国身份的材料寄出去,原因之一就是要讨好行动计划的某个决策层。以我过往的经验来说,这种情况在我们部门里面见怪不怪。
假如当我们打包的时候,加拿大同行检查文件的话,我们将会很难堪。这让我们很苦恼。所幸,加拿大人并没有检查包裹里的东西,我们避免了一场尴尬。
我们有六份加拿大护照和十二份美国护照。当然了,我们之前已经寄出去六份加拿大护照了,这就意味着我们两种准备的两种国籍都有富余。在第一套加拿大护照上,中情局驻加拿大的技术服务办公室技术人员已经伪造好了签证,证明持护照的人从某个欧洲国家入境伊朗。至于第二套护照,此次行动的签证保留空白。我和夏利奥将在进入德黑兰后伪造签证和入境印章,以便在最后关头见机行事。
最后,我们还准备了一份十分相近的材料使用和物品介绍的说明,以便参考——由非专业人士书写——里面包括世界各地的航班机票,以证明他们曾周游世界。离开加拿大时,我感觉良好,知道自己距离将“客人们”解救出伊朗又近了几步。
回到华盛顿后,我又开始准备计划的下一步行动,那就是飞往技术服务办公室驻欧洲办事处。我计划在欧洲跟夏利奥回合,准备我的假身份材料,并申请签证。
但是,在离开之前,我最后去了技术服务办公室一趟。在门廊行走时,我恰巧经过弗雷德·格拉乌斯的办公室。“门德兹!”他看见我后喊道,就跟海军陆战队的训练指挥官似的。“这次出去可不是玩去的!”他喊道,“你必须回到这里来做好管理工作——你可不再是执行任务的办案人员了!”
我知道格拉乌斯这是在劝我不要大意,这也提醒了我,要是稍微出点差错,我可就要翘辫子了。
第二天晚上,我和凯伦开车到杜勒斯国际机场。我跟凯伦尽量没让孩子们把我这次外出当成什么大事。他们那时都十几岁了,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操心。但是凯伦却不一样。我们一起走在机场的马路边上,我可以看得出来她很替我担心。我知道,她也明白我要去做的这件事情有多么重要。
我们之前也有过很多次道别。每次分别都差不多,并不是什么生离死别。我们的分离更像是一种传统,知道前面有危险,但是不至于无法控制。当然了,在危险失控之前,我们都觉得它可以控制。但每次因为类似的工作出差,都还是有一种沉重的悲伤。我4月刚刚出差参与解救“猛禽”的潜逃计划。和那个时候一样,这次凯伦知道我会有危险,但她从来都不知道我工作的具体细节。以前不知道,现在不知道,甚至以后也不会知道。这样最好。
我拔出车钥匙,看看凯伦。我把她拉到身边,亲吻了一下,抱了很久。我可以感觉到她的心跳。我们有一刻都静止了下来——相对无言。凯伦最后打破了沉默。“你得找一份正经的工作。”她说。
“这就是份正经的工作,”我说,“而且十分好的工作。”
“你得换份工作。”她说。
我下车把行李从后备箱里拎出来。凯伦也走下车来,绕到我开车门的地方。我把结婚戒指递给她——特工经常伪装成单身。我本可以把戒指放在办公室,或者放进衣橱。但是每次离别,我都习惯了把戒指交给凯伦。这个动作的意思就是说:“给,替我保管这个,我会回来找你要的。”我们从来都没有说过这些话,但是这就是我们的意思。
就在她开车走开,把我留在马路边上的那一刹那,我感到一阵悲伤。我希望自己能够履行自己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