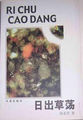离开大涝坝,在喧闹的发动机声中,浸着西北风的凉意,老万慢慢有了尿意,他弓起身,摇摇晃晃地在裆里掏了好久,才拉出那截肉来,拖拉机颠簸着,老万等了一会,却放不出水来。好几次,如果不是他抓住门框,就会被晃出门外。要是掉到拖拉机的履带上可不得了,老万的腿脚不太利索,这黑天黑地的野外,可没人帮他。
老万缩回身子,倒靠在座位上歇息了一阵。尿意是憋不回去的,想反,比刚才更紧了。他倚在门框上努力往外看,想看清走到哪儿了。整个世界都是黑的,根本看不清楚。管他呢,到哪儿都一样,得先解决要紧问题。老万刹住车,这次还熄了火。
没有“东方红”的吼叫,整个世界一下子变得异常安静,静得让人失去了所有的感觉。老万还不能适应这样的安静,他从座位上坐直身子,等了一会,听到西北风从远处刮过来的声音,这才钻出驾驶室。老万踩着履带跳下地,酒精做怪,腿软得站不稳,跌倒在地。慢慢地,他爬起来一瘸一拐地向前走了几步,掏出裆里的东西放水。过了好久,还没尿完,他失去了耐心,觉得眼前有几个黑影发出刷刷的声音,晃动起来。老万身子一抖,尿水洒到了鞋上,脚背微微热了一下。他睁大眼静静看了一会,发现是几丛堆积的玉米杆,西北风吹得干枯的叶子刷刷响,晃动的却是老万自己,玉米杆根本就没动。
大惊小怪。这个地方连狼都不来,纯粹是自己吓自己。
老万笑了一下,正常放水。尿的时间很长,老万闭上眼都快睡着了,过了好久才感觉身上利索了。抖抖索索提上裤子,已经适应了黑暗的眼睛才看清这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大会战。
刚开荒时,父辈们曾在这里搞过大会战,男女老少唱着歌,比赛开荒挖地,年轻人为了比拼,在路边挖了不少地窝子,白天晚上轮流干,临时住在地窝子里。
大会战就成了这里的地名。
大会战对老万来说,有着刻骨铭心的过去。他往前摇晃了几步,在“东方红”灯光醺染的范围找寻当年失足的那个塌地窝子。那里长满了干枯的野草,像一片黑乎乎的坟堆。老万的腿脚不灵便了,眼神却出奇地好,摇摇晃晃地在乱草堆里走几个来回,找到了那个塌地窝子。老万捡个石子,狠狠地扔过去,他听到石子掉落的声音,沉闷,清冷。石子落下的地方,就是老万成为瘸子的地方。
那时,老万还是小万,二十郎当岁,从部队复员回来,垂头丧气打不起精神,因为女友腊香被组织出面嫁给了革命烈属的弟弟陈有亮,作为弥补,老万当上了农场的民兵营长,这下,他不用下地干活,整天带着基干民兵在场部一二一走队列,扎着武装带在田地里巡逻,提防阶级敌人搞破坏。这样的待遇给了老万极大的安慰,慢慢地,他似乎忘记和腊香还有那档子事,除了有时看到腊香和陈有亮走在一起,他的眼神会暂时游移外,腊香就像梦一样被留在了昨天。他的情绪很快被民兵营长的职务调动起来,精神饱满,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尤其是大型集会或者搞活动,他带领大家喊口号时,脖子上的青筋暴得老高,那高昂的状态,绝对吸引大家伙的眼球。能在农场成为一个人物,此处失彼处得,老万想着,老天也算是公正的。
那年秋天,情人田里的棉花差不多快收完了,一片灰黑色的棉花丛,中间穿插几缕败绿,零零落落的几个没开的花骨朵,很壮观也很苍凉。这样的季节,却挡不住偷情的男女,基干民兵抓住了一对搞破鞋的。场部要在现场开批斗会,老万奉命召集剩余的社员,列成三路纵队,喊着号子,踏着步子,向情人田开进。作为领队,老万感觉像个老师似的在队列前带着学生走路,喊几声口号不过瘾,便离开大路,一个人走在旁边的田地里,像带着一支正规部队的首长,时不时地冲着大家挥一挥胳膊,喊几声口号。一路上,总听着后面的队伍喊得不够响亮,老万就倒退着一边踏步子,一边扯开嗓门给后面鼓劲。这支不专业的队伍气氛确实被老万调动得热烈起来。当时没人提醒,或者有人提醒了,却被喧腾的口号声淹没,反正,老万激昂地喊着口号,突然间就不见了,后半截口号声从蹋地窝子里传出来,大家才知道出事了。
老万从掉进地窝子的那一刻起,注定他再也当不成民兵营长了。他的一条腿摔折,再也踏不出整齐的步伐了。
从失去女友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不久,老万又失去了风光的民兵营长职务,场长担心他受不了这个打击,愁得头发都白了几簇,不知怎么安排老万才好。事实上,老万的确受不了,自暴自弃,脾气大得见谁都想骂。场长和颜悦色地对老万说,除过民兵营长和这个场长外,让老万随便挑,他挑中的绝无二话。怎么说,老万也是因公受的伤。
老万毫不犹豫地挑中“东方红”驾驶员的位置。拖拉机手不用踏步子,瘸子照样能当,况且“东方红”的油门用手掌控,用不上腿脚。场长当即愣了,“东方红”当时是腊香的丈夫陈有亮在开,场长以为老万是故意挑那个位置。谁让陈有亮夺了老万的女朋友呢。老万不管场长怎么想,他就是想做“东方红”的驾驶员。没办法,场长只好做陈有亮的工作,你陈有亮不能啥事都占一头,娶了人家的女人,就把“东方红”驾驶室让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