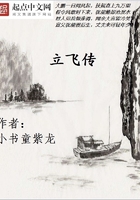不过,日本人既然常常表现出极强的“自尊”,为何在美国人面前就可以放弃“自尊”?这是值得探究的现象。对此,评论家大宅壮一说:往好听里说,日本人是一个极富弹性的民族;说得难听些,日本人是没有骨头的民族。其实,曾喊着要“一亿玉碎”的日本人倒并非没有骨头,只是非常现实而已。很多人在和日本人打交道后的一个印象是“欺软怕硬”,另一个是“翻脸无情”,都体现出了日本人的高度现实感。
列出了一大堆在日美军的宗主特权,那么,日本到底是不是美国养的一条狗呢?屏幕的下方打出了制作人员的名单字母,节目就要结束,北野武和观众说了再见。
有的问题不必说出答案。
欺软怕硬
和日本往来,不宜轻易示弱,指望同情和理解更有点冒险。因为欺软怕硬本来就是日本文化的特征。
日本人的劣根性中,这一条或许是最令人生厌和鄙视的。
某晚在车站,看到一辆出租车停下来,满头白发的老司机下了车,打开后门,试图推醒一个西装革履的男青年乘客。老司机大声叫着:“客人先生,客人先生……”男子始终如同酒醉酣睡般没有反应。我猜想他多半是装傻,就站下来看热闹。老司机连喊带推几十遍,只好回到驾驶席打电话报警。不出三四分钟,三名警察驾车赶到,老司机上前诉苦,一警察便走过来查看。就在此刻,奇迹发生了——男子双目睁开,生龙活虎地从座位上站起下车,仿佛一下子回了魂。我不禁莞尔,也证实了自己没有看错。生活中多加留意的话,类似故事或可一见,因为欺负弱者,畏惧强者,本来就是日本文化的特征。
东京的池袋附近是在日中国人活动较多的地域,一些日本右翼分子前些日子在此举行反华集会,高呼:“支那人滚回去!”“支那人都是罪犯!”顺便,他们还抨击以在日韩国人为主提出的争取外国人参政权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在日美军强奸了多少日本妇女,他们绝不会到美军基地前喊“美国佬滚回去”和“美国兵都是强奸犯”。对于美军或美国人在日本享有的超出日本国民之上的特权,他们也从未如此大张旗鼓地痛斥。看人下菜碟,莫过于此。
今天的银座依然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灯红酒绿的繁华商业区,然而,六十多年前,这里曾竖有一张巨型广告牌,上书“告新日本女性书”:“我们寻求新女性的率先协力,参加慰问进驻军的伟大事业。”实际上就是募集18~25岁的女性,为美国占领军提供性服务。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18日,内务省就用密电通知各地警察机构,着手为占领军筹建“慰安设施”。这是教人哭笑不得的日本式效率。尤其滑稽的是,这个官方性质的卖淫组织在皇居前的成立仪式上宣称:“我等并未有损气节或出卖灵魂,只不过尽不可免之礼仪,并履行条约中之我方义务(可美国与日本签订的条约中并无要求为军队提供性服务的条款),为社会之安宁作出贡献。”该机构名为R·A·A,每名日本女性每天“接待”15~60名美国士兵,直到美军因性病激增下令取缔。R·A·A的一大“成就”居然是为了治疗性病,美国首次将青霉素的专利卖给了日本公司。
在人类的武装冲突历史上,针对对方女性的性暴力是一种常态,近年来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约翰·道尔的《拥抱战败》中指出,在占领军“全体日本妇女都是潜在的妓女”的观点下,原有的日本人“野蛮残暴”的印象,被柔顺逢迎的女性形象所替代,日本的“慰安政策”对日后的日美关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像日本这样主动“献身”胜利者的做法,特别是在进入民族国家时代以后,的确是最为独特的例子,或许只能从强者至上的文化角度来予以说明。
强者通吃,弱者受弃的价值观,在一定意义上是日本人拼搏精神的内在驱动力。可是,这种价值观极端化之后的另一面,就变成了欺软怕硬的恶习。今日的日本社会中存在很多针对弱势群体的福利设施和政策,舆论也对弱者加以同情甚至讴歌,但在本质上,日本仍然是一个强弱迥然、强者崇拜的体系,体恤弱者只是为了装点其文明程度。比如,已经在日本中小学校园中常态化的“いじめ(恃强凌弱)”现象,文部省对之的定义是:“对比自己弱小的一方进行持续的心理、身体上的攻击,因对方深刻的痛苦而感到快乐。”被欺负的弱者没别的错,就错在弱;而强者欺负别人也无须更多理由,皆因其弱。至于孰强孰弱,只是一个现实的判断。
在一家中餐馆吃饭,华人老板娘正教育看上去刚来日本不久的孩子:“谁要欺负你,就一定要还手。他们要是人多,你就抓住一个使劲儿揍。”这话糙,理却不糙。媒体采访一位加入黑社会组织的在华日本残留孤儿后代,他说因祖母是日本人缘故,七岁时来到日本进小学就读,遭到同学的谩骂殴打等“いじめ”。他看到父母忙于辛苦工作,也不愿让他们担忧,于是决定反击。当他将一名带头欺负他的日本同学打倒在地后,“いじめ”也宣告停止。
人要现实点没错,整天世界大同四海一家的那是狂想症,但欺软怕硬又无疑现实得过了头,看似精明到家,却不知强弱总在变动之中,早晚免不了吃亏。和日本往来,不宜轻易示弱,指望同情和理解更有点冒险。当然,我也绝非在赞赏愤青,没有什么比战斗意志大于战斗力的人更虚弱了。要想和日本这样的对手平等交流,还真没别的捷径,只要你不是弱者。
寿司为什么这样红
日本人的饮食结构中确实有比较健康的一面,但把生食和日本人的人均寿命延长扯到一起,更多的成分恐怕是商业噱头。
我不喜欢吃“生もの”(未经加热、盐渍的食品,主要指鱼、肉类),所以对其看法难免有个人好恶在内,爱好生食的朋友或有不同观点,我只是略抒己见而已。萝卜青菜各有所爱,食不同不相为仇。
有人初来日本,就对生鱼虾牛马肉样样垂涎,而我在日本生活十几年,仍无法适应刺身(生鱼片)、寿司等食物,有时作陪国内来客勉强吃一点,肠胃总要造反。或许是情绪上的抵触暗示了身体的反应,我总以为人类在进化中从茹毛饮血到用火加热,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没必要非得逆流而上。其实,生鱼生肉咱们古人也曾吃过,叫“脍”,后来因防疫等缘故而放弃。当然,基因中来自远祖的积淀,可能导致一些人对生食(本文用意皆不包括水果蔬菜)的偏爱,但要为之建构优越性理论就难免牵强了。
来日本那年夏天,关西地区爆出一个名叫O157的细菌食物中毒的大案,在学校食堂就餐的近万名学生中招,数人死亡。一时间,日本举国的“生もの”生意遭受重创,我打工的店铺临时撤下了菜单上所有的生食。O157的病因就是未经充分加热,但近年来虽然时不时仍有病例,大规模的集团感染少见了,舆论的关注程度也不热心。毕竟,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人类的记性是很健忘的。
生鱼片和寿司是日本人生食的代表,最大的危险应该是寄生虫,所以进食时配以芥末和姜,据说为了消毒。但据我观察,日本人当中皮肤病比例颇高,怀疑和生食习惯有关,后来读德国著名学者海因里希·施里曼一百多年前的《清国、日本游记》,发现他对日本人皮肤病和食用生鱼的关系有同样看法。一位日本朋友体毛比较丰盛,自嘲说刺身和寿司吃得太多,可见他们自己也有感受。
不过,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以寿司为首的日本料理在海外的流行。Sushi是英语中的专有名词,N多的好莱坞明星都说寿司是他们的最爱。寿司为什么这么红?
任何一种人类的“民族料理”,都不仅仅意味着食用价值和味道、原材料、烹饪方式的差别,更蕴涵着丰富的意识形态内容,特别是进入民族国家时代以来。波兰学者J·Cwiertka曾留学日本,专门研究日本和韩国饮食,他指出,所谓日本料理的概念,是和日本的民族国家概念一同打造出来的。给菜肴安上国籍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附加了这个国家的印记。比如说纳米比亚(信口借用)料理,很容易有蛮荒色彩;而说日本料理,就产生了精致的印象。
19世纪中叶日本开国之后,到过日本的西方人对JapaneseFood予以普遍恶评,简直到了“除非真的没东西吃,不会去碰那些难以忍受的食物”(英国军官亨利·诺里)的地步。然而,今天的日本料理,尤其是寿司,成功地打入了“第一世界国家的美食界”,成为中产阶级以上民众喜爱的异国风味。在第三世界国家,日本料理也常常具有高档食肆的身份。事实上,这个变化本身只能说明人类的无理性本质。
日本人的饮食结构中确实有比较健康的一面,但把生食和日本人的人均寿命延长扯到一起,更多的成分恐怕是商业噱头。很显然,生食和地球上其他长寿地域的居民并无必然联系。J·Cwiertka认为,寿司在日本以外最初的滥觞,是美国的加州。当地有为数不少的日本裔居民,但更重要的是,寿司被赋予的自然、健康、反传统意义迎合了此间声势浩大的“雅皮士”运动。“雅皮士”代表食物寿司因而登堂入室,成了高收入、高学历而又特立独行、热爱自然的“精英”们的宠爱。他们将这股时尚带到了欧洲,又进而影响了欧美的普通大众,以至于回转寿司的店铺如今遍布西方主要城市,有的华人餐馆也像模像样地搞起了日本料理。
在华人世界,日本料理的身价也比较高,连廉价快餐吉野家都跟着沾光,仿佛应了南宋哲人陆九渊那句话: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尽管那些生鱼虾牛马肉若出自纳米比亚人之手,很可能要被斥为“教化未开”。
哪怕附庸风雅
企业在商言商,却肯花费不小的金钱于社会文娱活动,尤其是一些阳春白雪的项目,看上去有附庸风雅之嫌。
某年亚冠去J联赛鹿岛鹿角队的主场,在体育场内墙壁上看到俱乐部的赞助商名单,有当地的十几家企业。和中国联赛俱乐部不同的是,日本各俱乐部以地域为依托,一般是由现地的多家企业共同出资协办,只不过彼此金额略有差异。日本男足虽然这些年来火热过几次,但J联赛俱乐部极少有赚钱的,大多是赤字,依靠企业赞助维持。那么,企业们又拿不到中国式的“冠名权”,为什么要掏钱呢?理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J联赛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是提高日本足球运动水平,第二是以体育文化促进国民身心健康,第三是推动国际交流发展。这第二条的责任,就落在了提供财力物力支持职业俱乐部的企业身上。他们出钱建设球队,丰富所在地民众的娱乐文化生活,是为了履行企业对社会应尽的义务。
曾和几位在日本活跃的前中国运动员有过交流,对日本企业在这方面的角色略有了解。日本的竞技体育除了职业化的棒球、足球等项目之外,大部分是企业在担任培养、训练运动员的角色。很多企业内部设有体育部或社会活动部,一方面以运动员担任企业形象宣传,凝聚企业向心力;一方面把这笔开销当做回馈社会的支出,因为观看体育比赛是大众性的娱乐。有的企业对运动员们的管理比较宽松,可以为他们的专业训练创造较多方便;有的企业还真的把运动员们当普通职工,一半的时间要花在工作上。当然,后者的做法对运动员退役之后的生活保障无疑大有裨益,无论如何也不至于沦落到去搓澡。
《体育日报》提到了日本体育界多年来流传的一句格言:“运动员应该甘于清贫。”这种说法的真正含义是要求运动员有一种求道般的刻苦精神,同时抗拒金钱的诱惑。当然,日本体育界亿万富翁大有人在,可穷人也确实有。获得过奥运女子马拉松金牌的野口曾长时间失业,靠失业救济金生活,连房租都负担不起。获得过柔道金牌的上野雅惠和获得银牌的横泽由贵都在三井住友海上保险公司上班,收入和一般薪族相同。位于大阪的玩具商米奇屋,支持着11名日本运动员,其中的野村在奥运会上曾获柔道金牌。米奇屋表示,每年用于这些运动员的经费是10亿日元,主要为了烘托公司“给孩子一个梦想”的理念。这些运动员平时不用来上班,但要出席社内大型活动。
企业办体育,是日本体育事业的最鲜明特色。以前看到的数据统计,雅典奥运的日本代表团中,居然有一半以上的身份是企业员工。但是,企业办体育并非没有波折,最大的不利影响莫过于经济状况的恶化,就只好削减预算与规模。近年来,日本竞技体育在奥运等场合的表现平平,多少触动了各级政府机关对加大体育事业投资的念头。不过,总体来讲,体育作为企业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一段时期内仍将是主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