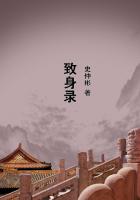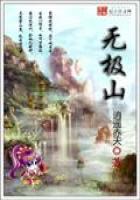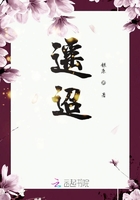可以根据演绎理由假定:这些欲望的外在的、后天的决定因素虽然是确切存在的,但也同样无疑是很脆弱的。大多数理论家认为或假定,爱的需要是以生理需要的满足为基础,并通过条件作用形成的。例如,我们学着去爱,是因为我们爱的人过去是食物、温暖、保障的给予者。这样,这种派生需要论就必须坚持这样的主张:知识、理解和美的需要是以生理需要的满足为基础,并通过条件作用形成的,即它们过去和现在都是代替食物的信号,可是通常的经验几乎根本不支持这种论点。不难看出,它比类似的爱的后天获得论更站不住脚。
本能的文化标准(我们现在说到的这种反应是独立于文化的吗?)是一种决定性的标准,但不幸的是,我们还没有明确的资料。就其本身而言,它们支持我们考虑的理论,或者与我们的思路一样。然而,必须承认,换一个人审阅同样的材料,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由于我们的现场经验仅限于与一群印第安人有过短期接触,而且由于问题取决于人类学家未来的发现而不是心理学家的发现,在这里我们将不再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考察。
基本需要本质上是似本能的原因我们早已经谈过了,并且上文还提到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些需要受挫会导致精神疾病,这是所有临床工作者都同意的。然而,对于神经质的需要,对于习惯、吸毒、对熟悉事物的偏爱以及对于工具性需要来说,这不是事实,只是在某种特殊的意义上,这对完成行动的需要和表达能力的需要来说才是事实。至少,对于这些形形色色的需要能够根据实用或实效来区别,并且应该基于理论和实践的原因来加以区别。
假如价值观造就会创造的人,并使人接受它们,那么,为什么某些价值观念在受到挫折时会导致精神疾病?我们学会一日三餐,学会道谢,学会使用叉匙、桌椅,我们穿着衣服、鞋子,夜晚睡在床上,说英语,我们吃牛肉、羊肉,而不吃狗肉、猫肉,我们保持清洁,为等级竞争,对金钱挖空心思、绞尽脑汁,然而,这一切强大的习惯在受到挫折时可以没有痛苦,甚至还有积极的结果。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泛舟或野营时,我们通过轻舒一口气抛开这一切,承认它们的非本质性质,但对于爱、安全或尊重,却绝对做不到这一点。
很显然,在特殊心理学和生物学中,基本需要占有重要地位。它们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基本需要必须得到满足,否则我们就要得病,谁要是否认这一点,就得拿出证据说明它们不属于似本能的需要。
基本需要的满足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后果:产生有益的、良好的、健康的、自我实现的效应。有益与良好这两个词是从生物学的意义而不是先定的意义上来说的,可以用操作来给它们下定义。只要条件允许,健康的机体本身就倾向于选择并努力获取这些结果。
在论及基本需要的满足问题时,我们已经概述过这些心理上和身体上的结果,这里没有必要继续考察下去,只是仍需要指出,这一评判标准并无奥秘、荒谬之处。可以很容易地以实验甚至工程为根据来验证这个标准,我们只需记住,这与为一辆汽车选择合适的汽油是一样的道理。假如一辆汽车使用了某种汽油发动得更好,这种汽油对于这辆汽车就比别的汽油更适用。普遍的临床发现,当安全、爱以及尊重得到满足时,机体就发挥得更好,感觉更敏锐,智力使用得更充分,更能使思维正确而缜密,更有效地消化食物,更少患各种疾病,等等。
将基本需要满足物与其他需要的满足物区别开来的是它们自身的必需性。出于本性,机体自己指明了满足因素的固有范围,这是不能由他物替换的,而这对于习惯需要,甚至神经质需要却是可能的。也正由于基本需要满足物的必需性,最终将需要与满足物联系在一起的是疏导作用而不是任意的联系。
对我们的目的而言,心理治疗的效果是相当有利的,似乎所有主要的心理治疗方式都培育、促进、巩固了我们称为基本的、似本能的需要,同时削弱或彻底消除了所谓神经质的需要,直到它们取得心理上的成就感。
例如在罗杰斯、弗洛姆、霍尼等人的疗法中,这些重要的事实可以使他们直接宣称自己能使患者恢复自己内在本质。因为这意味着,人格本身具有某种固有的本质,它不是由治疗家新创造的,而是由他挖掘出来的,以便按它自己的风格成长、发展。如果顿悟和压抑的解除会使反应消失,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个反应是异质的,不是内在固有的。反之,如果顿悟使反应更强烈,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本质的。同样如霍尼所推论的,假如解除焦虑使患者变得更富有感情或更少怨恨。对于人的本性来说,这就表明爱是基本的,而仇恨则不是基本的。
关于动机、自我实现、价值、学习、一般认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文化适应与反文化适应等等理论,从原理上讲有一批宝贵的资料。遗憾的是,这些关于治疗转变的有意义的资料还没有系统地积累起来。
基本需要的重要地位,已经由对自我实现者进行的临床以及理论的研究证明得很清楚了。健康的生活取决于这些需要的满足而不是其他,并且,很容易看出,对于似本能假设所要求的满足,自我实现者是在接受冲动而不是控制冲动。总之,我们还必须深入下去,就象研究治疗效果一样。
研究现场调查的工作者们最先表现了对人类学中文化相对论的指责。他们感觉到,文化相对论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异夸大了,把这种差异说成是相互敌对和不可调和的,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我们在旅行中获得的第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印第安人首先是人、个体、人类,然后才是印第安黑脚族人。虽然区别的存在不容置疑,但与共同点相比,差异是表面的。不仅印第安人,而且记录文献中描述的所有种族几乎都有自豪感,愿意受人喜爱,追求尊重和地位,回避焦虑。另外,我们自己文化中可观察到的素质上的差异,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如智力的高低,意志的强弱,积极性或惰性,沉静或激动等等。
甚至在区别很明显的地方,也可以证实这种人类共性。因为这些区别往往可以马上为人所理解,并被认为是任何人在同样情况下都会有的反应,与对失败、焦虑、沮丧、胜利以及临近死亡的反应一样。
这种感情有点模糊不清,无法肯定是科学的,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上文已经提出和下文还要提出的假说,例如:似本能需要的微弱声音;自我实现的人的不同寻常的超然与自主力,以及他们对文化习俗的反抗;健康概念和适应概念的区别等等,那么,重新考察文化与人格的关系,从而更加重视机体内部力量的决定权,看起来就是成效卓著的,至少对于较健康者是这样。
假如一个人在成长时并不考虑这一结构,他的确不会摔坏腿脚,也不会立即出现明显的病态。然而,得到大家一致公认的是,或迟或早,或隐或显,病态将会出现;可以引用普通成年人的神经病作为说明早期对机体内在(虽很微弱)需求挫折造成有害后果的例子。显而易见这是确切的。
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人格和品质不被破坏而与文化习俗抗争,则应该是心理学和社会学中一个很有意义的、值得研究的课题。很快就能顺从于自己文化中的摧残力量的人,即适应性强的人,也许还不如那些违法者、罪犯、神经病患者健康,这些人也许正是以自身的反应显示了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反抗折断自己精神支柱的文化。而且,思考这一理论的同时还出现了一个乍看起来似乎是荒谬之极的反论。教育、文明、理性、宗教、法律、政府统统被大多数人解释为本质上约束本能的压制力量,但是,假如本能惧怕文明比文明惧怕本能更加严重,假如我们仍希望产生更完善的人、更完善的社会,我们就应从对立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教育、法律、宗教等至少应起保护、促进、鼓励安全、爱、自尊、自我实现等似本能需要的表达和满足。
似本能的基本需要有助于解决和超越许多哲学中早已经提出的矛盾,例如自然性与社会性、先天与后天、主观与客观、独特性与普遍性之间的矛盾。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揭露治疗、自我寻求治疗、个人成长、“灵魂寻求”技术都是一条发现自己的客观生物本性、动物性和神经性,即自我价值的道路。
不管是哪一个学派,它的大多数心理治疗学家都认为,当透过神经病症深入到那个原本存在,但却被疾病的表层所覆盖、掩藏和抑制的核心的时候,他们是在揭露或释放某种更基本的、更真实的、更实在的人格。当霍尼谈到透过虚假自我深入到真实自我这一问题时,她的这一论述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关于自我实现的论述也迫使一个人内心的状态变得真实或实际,虽然是以一种潜在的形式。对认同的追求与“成为自己真正是的那个人”一样,也是同样的意思。使自己成为“充分发挥作用”或具有充分的独特性的和具有真正自我的人含义也是一样。
中心任务显然就是要意识到自己真正是的那个人是在生物上、气质上和素质上作为一个特殊族类。这正是花样繁多的心理分析所要做的事,即帮助人们意识到自己的需要、冲动、情感、快乐和痛苦。但这是一种个人自己内在的生物性、动物性和种族性的现象学,它通过体验生物性而去发现生物性,我们可以把这种生物性称为主观生物性、内省生物性、体验生物性等等。
但是,这就等于是对客观性的主观发现,即对种族所特有的人性特征的发现。它还等于是对一般的和普通的事物的个人的发现,是对不受个人影响的超越个人的(甚至超越人类)的东西的个人的发现。一句话,我们可以通过“灵魂探索”,通过科学家的大量的外部观察去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研究似本能。生物学不仅是一门客观的科学,也是一门主观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