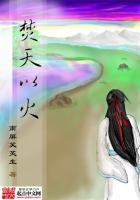早上醒来,第一次睁开眼睛,马上就要闭上。好像潜意识里总有一种恐惧感,对未知的恐惧。
跌跌撞撞头发蓬乱衣衫不整地奔向卫生间,看到卫生间的镜子里有一层厚厚的雾气,我看不清自己的脸。
来不及吃早点,便冲向学校。飞快的样子。家是圆周的一个起点,经过固定的冗长的轨道旋转,黄昏来临之后,又会回到这里。
我,18岁了。
编辑打电话来向我约稿,主题是“最美的日子”。写散文。我突然觉得有些晕眩,好像这5个字让花园里所有的花都开始枯萎,忧伤而疼痛。努力在思想里寻找一些符合标准的词语,可拼在一起,发现还是碎片。我的手有些颤抖,害怕流淌出来的是更多的无助。
打开门。出去。看到天空里到处都是阳光,蓝色的,闪光的。街角里坐着那些染了头发颓然抱头的孩子。来往的车向城市吐着肮脏的气体。阳光太亮了,以至于让我眼前…片漆黑。
每天都会收到很多信,来自全国各地。他们或她们说喜欢我的文字。我会很仔细地看每一封信。从信到邮票,再到信纸。这些细节,是组成幸福的理由。
间或有几封信会寄来照片。照片上的孩子,笑得灿烂而甜蜜。是我很久没有看见过的微笑。
一般利用夜晚的时间写作。深信夜晚的空间比白天有刺眼阳光的空间广阔。也许是更能接近回忆。
所以这些文字就像荒原上的植物,野性而不加修饰。
一个读者写信给我,你的文字美丽得有些残忍。我想他应该是觉得安慰。
有些大学的学生写信给我,说很多温暖的话,让我突然对很多失信已久的东西又充满希望。我知道那会是很快乐的。
由于过于信任太过于温暖的东西。总是在夜间裹着被子跟朋友打电话。可能有一段时间,在电话这头滔滔不绝;有一段时间,则沉默不语;或不停地喝自来水。觉得很温暖。
因为这些,我在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刮到的伤口,将不再疼痛。
为了自己和爱你的人活着,我始终感到自豪。
总喜欢呆在地铁里等车的感觉。从一条高高的台阶上来,灯光黯淡,人影晃动。
常看见一些年轻的孩子成群地坐在台阶里聊天或者沉默。站口的风轻轻经过。他们的声音有些嘶哑,然而很清晰。是一种年纪轻轻的新。有时候看到一两个孩子孤独坐在角落颓然抱头或抽烟。衣着凌乱。伴随黑暗地道里一闪而过的明亮地铁的车灯。
很多次都看见一个孩子,头发是淡淡的绿,穿宽大的衬衫,显得骨架突出,穿有破洞的牛仔裤,拿一把吉他拼命地弹,头在轻微地摆动。这些音符是愤怒的,然而在这个城市的底部才能爆发,出地铁站口,刚才轻轻经过的风已经找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的喧嚣和经过身边的陌生的脸。
于是突然觉得孤单。有些东西遗忘在了地铁站里,但却带不上来。
“颓废”是一个很能让血液变得不平静的词。甚至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试着把自己沉浸到这个词中去。然而不能,因为痛苦。我的性格有着慵懒但却上进的成分。
高二的时候和一个很典型的颓废男孩坐一起。他的个子高而瘦,骨架突出,满口脏话,走路的时候头向前倾,象任何一个街上的小痞子。他没日没夜地上网,从不听一节课。他有自己的一帮朋友——和他一样的厌恶学校的人。每天早上,他都会从网吧赶到学校抄作业,吃一块钱一包的干脆面。吃面的时候,长长的脖子朝四面扭动,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确定老师不在,就飞快地揪一团面块,塞进嘴里。上课的时候他往往睡觉,或者和周围的人讲些黄色笑话。在课堂上,他那种无视旁人的尖刺的音量,穿过耳膜,微微发痛。
有时我跟他说话,他总是眼神恍惚。总是叫好几声,他才答应。一个捉摸不透的孩子。
会考前夕,我每天坐在晒不到阳光的屋子里,没天没日地背书。他坐在我身边。有时我背一段时间,看见他从书包里拿出书本,读了几声,又丢到一边。
他仿佛一直是在睡觉,或者讲些粗俗的黄色笑话。这些碎片构成了我对他的全部印象。
我试着接近他,他总是礼节性地回应。我触摸不到他的心灵。
考试发卷子时,分数的极大落差,让他在很远的地方看我。这是他对我说的。
吃干脆面、睡觉、上网。这是他每天生活的全部内容。他的手臂苍白。
这是不属于我的世界。让我恐惧和不安。但又有一种流淌的平静。这并不矛盾。
青春有很多种,并不是都能融合的。
城市里总会或多或少散发奢靡的气息。城市里的孩子就在白云游动的天空下成长。
在街道中穿行久了,会有窒息的感觉。所以经常爬上高楼的顶部,可以清楚地看见大片大片的蓝色。让人很舒服。被条条框框限制久了,就向往松弛。
想到12岁的时候,自己对着天空许下理想,要当个旅行家。然而,理想现在开始模糊。
爱从高楼往下看,是因为能看见温暖的城市里,我的10岁时清澈的脸;我丢失在大雨中绣有好看花边的古式伞;我12岁时的诺言。它们通通随风飘逝,直到毫无踪影。
那些透明的年纪。
我是个有怀旧情结的人。对一些往昔的旧杂志、旧唱片以及往昔的气味和颜色等都有敏感的反应。保存记忆里一些美好的东西,会让幸福不至于太平庸。听过一个青年画家在一个座谈会上的讲话,说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忘记自己年少时的一些故事,它们是流着新鲜血液的百合,吐露着源源不绝的灵感。
当那些回忆成为飘落的花瓣时,每一片都会蕴藏不能忘记的段落。
朋友跟我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学会生活?
生活是个我不能想象的概念。在我的城市中,我几乎不能抚摸它。它是一朵绽放的鲜花,盛开在遥不可及的别处。
LHY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头发顺着脸颊垂下来,低头的时候会遮住大部分脸,夏天的时候穿很好看的花格子衬衫,不扣扣子;走路时一摇一摆,好像随时就会倒在地上;说话时声音纤细得像刚出声的小猫,甜甜的样子。
每次上体育课,我们都爬到教学楼的楼顶。我们踩在木制的有裂缝的地板上,它们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30年代的装饰,让旧旧的时光开始沉淀。阳光透过有裂缝的木板射出来,被分割成很多线条。
LHY会眯着眼睛看太阳刺眼的光,有一块一块的暗影投射在她脸上。她会告诉我她最喜欢的城市,那个烂漫得有些出格的城市。
“我会一个人在下午去咖啡店喝咖啡,加奶的那种,一直坐到晚上。”
“我要自己租一座房子,用粉红色的油漆刷墙壁,上面画很卡通的涂鸦。”
“我要去淮海路购物,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她讲着讲着,就发出“咯咯咯”的笑声,像糖一样。窗户外面,缓和的风吹动着云淡风清的日子。
我们是一群没有未来的孩子,有了理想就会快乐得很。如果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里,生活就会变得很平庸。
终于,我和很多叛逆的孩子一样,沉迷用音乐来寄托自己的情感。
一开始,我钟情于抒情摇滚。因为很温暖。我经常在学校旁边的唱片店找那些已经年代模糊的唱片,比如披头士。那些明亮的年轻的声音能让气息变得很顺畅。常常带着耳机走在大街上,在混浊的空气中,忽略了喧嚣的过往。觉得画片是纯净的,音符流动。后来渐渐开始听黑人的灵歌,感觉到的是原始的气味。一切充满商业气息的音乐都开始变得俗气。
有时,过于精致的事物往往让人没有安全感。如果是初始的样子,反而会更美好。
我和LHY坐在电视机前抱着一大袋薯片和白开水,看MV。琳恩·玛莲拿着吉他走在一个孤单的城市,清脆的声音划过城市里那些陌生人的睑。我感到有清凉的风吹过耳边,是那种城市底部的风。
你们的乐队怎么样了?最近有新作吗?LHY转过头看我。
“我写了一首歌,在给甜菜编曲。”
“到时候我一定要一个人听。”
“一定。”
我把这个叫做毛球的乐队的合影拿给LHY看。LHY兴奋地跳起来,好酷。
照片上四个男孩笑得和当时的阳光一样灿烂。站在最前面的两个孩子是甜菜和木木。
“甜菜是个极有音乐天赋的男孩,留着清澈的短发,笑起来甜甜的,有个酒窝。他很小的时候开始喜欢上钢琴,现在还执著地弹,尽管已经高三了。他擅长编曲。所以毛球乐队的很多歌都会由他参与制作。他是一个优秀键盘手和编曲人。”
前排右边的男孩是木木。他是个很帅气的男孩子。有着健康的寸头,笑起来很迷人。他夏天的时候穿着运动短裤和衬衫去打网球,会引来很多女孩子的目光,一些富含着青春萌动的辐射。他的低音吉他会让音乐变得狂野起来,有一种运动过后汗水的味道。
“后排留长头的男生是赫洁。一个有着女生名字的男生。从小在孤儿院长大,额前的长发常常遮住眼睛,有时颓废,有时张扬。总觉得他心里有块暗暗的东西。但是他是最执著的一个人。有次为了买一把心仪已久的小提琴,在琴行缺货的情况下,天天去等,坚持了三个月。会很多乐器。有时写词,残酷而寒冷。”
“最后的一个男生站在你面前,他叫Mickey,乐队的主唱,擅长写歌。是个像小孩子一样充满幻想的男孩。”
LHY呵呵地笑起来,“我知道,你们是毛球乐队。”
我不知道有些事情以后会怎么样,只是觉得现在我们是一群没有未来的孩子。就像从高楼向下望去看见的那些飘泊门不定的东西。
当我们不再觉得青春冗长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衰老。
有一年夏天走在东门的街道上看着城市容器的底部人们穿梭来往如同鱼群。他们的脚印在干净的街道上留下痕迹,然后逝去。我发现我没有留下什么给自己。
去北海道的时候,浑身只穿了一条短裤和一件T-shirt。虽然夏天炎热的温度像大海的波浪,起伏汹涌,却觉得清爽,因为在北海道看见很多树木和公园,那些风景天然的地方时常有老人手挽着手散步,我看见他们把青春留在树叶的尖端,闪闪发光。很多可爱的小孩子在阳光底下微笑,是从心底渗出来的愉悦。那些被现实消磨掉的时光散发出风一样的味道。
后来,我走进日本的一所不知名的高中。坐在双杠上听整洁的教学楼传来下课的铃声。校园里所有年轻的气息都被它震醒。穿着校服的高中生们走出教学楼,时间就变得无限长起来。有些男孩子,留着长发,如木村拓栽的翻版。他们手里的香烟升腾出浓浓的雾气,让我看不清他们的脸。他们几个人一群站在校门口聊天,像任何一个黑社会的小头目。燥动不安的气息从他们鼻孔和眼神里像液体一样被喷洒出来,然后被蒸发掉。我想起有个被我用“颓废”形容的男生。他会上课睡觉和讲黄色笑话。他曾经坐在我的身边,但我触摸不到他的心灵。
头顶的蓝色天幕曾经流淌过美丽的日子。但毕竟只是曾经。
有一段时间,在电台主持一档中学生的节目。因为是直播,所以每次必须提前1个小时到电台做准备。
有很多次看见一些可爱的小男孩和小女孩。他们背着书包,穿着牛仔和时尚的外套,颜色鲜艳,鞋带松散地坐在台阶上。看见我就跑到我面前问候,最后聊一些很边缘的话题。他们会在很晚的时候去48层楼的楼顶大喊青春万岁。他们会买很多温情的摇滚在酒吧醉生梦死。他们游走在城市边缘而忘却了很多。他们还年轻。
坐在直播间,带上宽大的耳机。对着话筒,节目开始。我能感到自己的声音在夜间冰凉的空气中绽放出一些灯心,然后城市里的孩子会打热线来点亮它们。我们说很多很温暖的话。现在的孩子真的缺少沟通,如果给他们一个值得依赖的话筒,他们会源源不断吐出许多令人惊异的文字。
只要和孩子们讲话,我就会觉得温暖。
虽然这是个告别和隔绝的时代。
从16岁开始,每年过完生日的晚上,闭上眼睛都会想到死亡。我感觉周围很多冰冷的气息都在盘旋上升,不知道要去哪里。意识划过午夜陡然降温的墙壁,渗进一种温存之中。想到未来还是要走很多的路,说很多的话,写很多的字,虽然以后的事谁也无法预知。
一次去聋哑学校。看见很多笑容清澈的孩子,用手指比画着他们的心声,嘴唇极力地张开,我却什么也没听到。也许有些人天生就没有得到上帝的宠爱。但是,我看见他们在画画。那种颜色混合着调色盘里的气味,成为一团火,燃烧。我想到我和他们一样呀,我心中原本也有一团火的。后来,我也慢慢变得安然,不再讨论宿命或者无常,一切都再也平静不过。
生活像水一样,流走了我的遗憾,有一天,也会流尽我的青春。
几个月前,我一个人坐火车去西安。看到灰黄色的山被炸开一道道伤口,坚韧的边缘直指天空。有一场不能呈现的痛苦。夜晚,躺在晃动的车箱里,将被子裹紧,把头埋进温暖的黑暗里。周围像海水一样荡漾着一个人的孤独和自由。窗外那些离我很远的星星,它们散发的光在向谁诉说着温情。
凌晨3点,火车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伴随着火车绵长的汽笛声,轰隆的感觉瞬间停止。猛然想到爱情,少年的爱情,它们像樱花一样在记忆里飘舞,找不到方向。LHY说她喜欢的男孩会在黑暗中紧紧抱住她,男孩的体温就像电流一样迅速在她身上蔓延。LHY会把头死死地埋在男孩的怀里。那一瞬间她可以什么也不要。
我把头温柔地靠在棉枕上,样子就像是《小王子》里那只等爱的狐狸。
此刻,爱情对我好像只是一种幻灭的感觉,轻轻一触,如烟溃散。
到达西安,我睡了一个很好的觉。但是却觉得自己仍在来回不停地晃动。
看到秦始皇兵马俑的一瞬间,我的流海遮住了眼睛。那些布满历史尘埃的人俑,让人想到几千年前在战场上厮杀的场面,一个个年轻的生命如碎石一样飞溅四处,在告别青春的同时告别生命。
去皇帝陵祭奠祖先的时候,我闭眼祈祷,虔诚得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睁开眼睛,我感到什么东西正在迅速溜走,伸出双手也抓不住。
我知道的,我停不下我的流年,总有一天时光会轻轻悄悄地消失在视线尽头。现在的每一秒我都要让它绽放出它应有的光,像12岁时高楼顶部的阳光。
终会有一天,我会真正地安然起来。离开宿命和无常,一切都再也平静不过。那些从楼顶看到的城市上空飘浮不定的东西;那个颓废的捉摸不透的男孩;那个甜甜的LHY;那个毛球乐队……它们也会一闪即逝,如同星辰。
烟花般的过往只能留在回忆里。但是瞬间的美丽却是永恒的。
有时,一些东西虽然和时间一起消磨掉,但还可能存在于我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