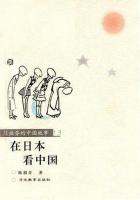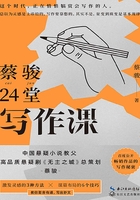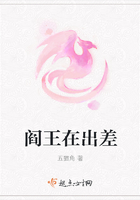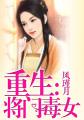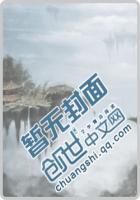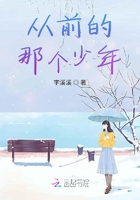前面我们已经说过,韦伶是一个有着自觉的女性意识的作家。虽然她的作品和时下一些标准的女性主义创作颇不相同,但她是很自觉地将自己的作品作为一种现代的“女书”来写作的。在《走神女孩》一书的《后记》中,她曾称自己的作品是为她们“女儿族”写下的文字,是“平日姐妹们的叨叨”。说“叨叨”当是自谦,且作者的作品是用很清雅的书面语写成,不太具有我们一般印象中“叨叨”常有的口语性、日常性、琐屑性。我们或可将作者这种言说上的特点称为絮语性。絮语是一个亲密的小圈子里的人(特别是女性)常见的说话形式。中国古代一些“女书”性的作品好多也用这种语言写成。絮语首先指言说内容的某种私人性、小圈子性。在中国传统“女书”中,就是其“闺阁”特点。韦伶写的是少女,它的很多内容就是少女那个圈子里特有的。如我们前面谈及的女孩关于自己身体变化的自觉;女孩面对陌生的外面世界又兴奋又慌乱的隐秘感觉,特别是女孩在月光下的舞蹈:“那时我们确实没有花时间去认真排练一个完整的节目,也并非只是聚在一起练舞。女孩们上瘾似的离不开这种聚集,真真是大家心中朦胧有一种默契,渴望在一起用舞蹈的身体进行一种体验、一种交流、一种发泄和表达”,以及因为舞蹈训练中断而产生的“那种压抑、委顿,以及身体情感方面,感觉到的无法言说的‘进不来、出不去’”的状态。由于这种内容上的私人性、小圈子性,絮语往往有一套自己的语言,如特殊的词汇、句式,包括一些只有那个圈子里的人才懂的“隐语”。韦伶的作品毕竟是公开出版、主要给少年儿童看的,不像传统女书主要只在闺阁中流传,隐秘性并不明显,但也有一些有女孩、女人倾向的语言。“每当蠢蠢萌动的季节,融融春色下总要绽放一段花期,总要在渐熟中等待又惧怕采摘的,是树,是女孩”,这话每个花季女孩都能心领神会,同年龄的男孩恐怕就未必懂了;“今天下午,小咩和我又去温泉游了泳……(小咩)一边走一边抖落着头发上的水珠,目不斜视地穿过走廊上排队洗澡的女人群。”坚持把“游泳”和“洗澡”那么界限分明地区分开来,只有懂得小咩们的特定心态才能懂她们特定的语言。与此相适应,絮语还是一种语调,一种由这种言说方式创造的特定效果、氛围。絮语是亲密者之间的促膝交谈,其效果有时不在交谈的内容而在交谈本身,故往往有一种特殊的亲昵性。韦伶写少女,她的许多作品都包含着她自身的生活体验。可是,当她经过岁月的洗礼来重述当初的感觉的体验时,她突出的不是现在所站的这个点,而是突出当初经历时所在的位置。即使是以今天成年的自己的身份出现,也是像对待少女时的自己一样对待现在通过作品和自己对话的人,娓娓叙来,仍有一种面对“自己人”的真挚和坦诚。如《那夜的幻殿》《浴月舞幽影》等,简直可以听到作者和读者心的撞击的声音。这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影响到作者的文体。韦伶的作品主要是小说和散文。但二者的界限却并不明显,抒情中有叙事,叙事中有抒情,不强调时间而强调空间,不侧重过程而侧重体验,如《那个夜》《相望的风景》《裸鱼》等,可以说它们是小说,也可以说它们是散文。这可能也是传统“女书”常见的特点。
韦伶作品在表现层面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受其他艺术类型的影响,或曰对其他艺术类型表现手法的积极借用。其中最主要的是舞蹈和绘画。韦伶显然是学过这两门艺术的。特别是舞蹈。她在多少年以后的散文中,还那么真切地回忆起当时的体验,那么真切地叙述当初的沉浸和陶醉。舞蹈不仅从叙述对象、叙述者自身感觉的角度影响了韦伶的作品,在艺术表现上,也从中获得了一种和月光下少女舞蹈相类似的从容:舒缓和优雅。“她可以惊喜地看着自己逐渐饱满的手、臂、腿,在超凡的弹跳舞动中划出漂亮的线条和亮光。她可以在舞蹈中松弛或制造一种伴随青春的紧张,将压抑未渲的情感,通过无言的身体动作,激烈或舒缓地发挥出来。她可以在野外翻滚扑卧和飞跃中,那样临近那样刻骨地与土地、荒草、阳光和熏风接触交流……”从这些修饰得极好的句子中,可以分明感到少女们优雅舞蹈的韵律、节奏。绘画也如是。比如我们在前面谈及“相望”在韦伶艺术结构中的重要意义,在某种意义上,“相望”是一种造型,一种构图,典型地体现着画面的平衡、对称。还有作者关于走向成熟又尚未成熟的女孩的经典比喻:一幅肖像,半边脸绿,半边脸红,中间一道空白的裂缝。也只有对现代绘画颇有感悟的人才有这种联想。绘画对韦伶作品的影响,在色彩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如《裸鱼》对五彩海子的描绘,简直就是一幅色彩、光线都极鲜明且有层次感的画:“眼形的湖不太深。那团紫色氤氲,正从湖中心的石穴中雾一样散出来,向湖的四周扩散。湖水从中心到外环逐层变成了孔雀蓝、翠绿、浅黄,然后浅浅淡淡地渗入湖岸的石柱中去了……湖的水平面上,有一片片的暗红在波动,是那种比火更浓更重的秋叶倒映的暗红,是这一片紫水里所不存在的红色,如虚幻的梦一样,薄薄地飘在湖面上。鱼们现在浮上来,不为寻火花,是诱于湖面浮动的一片片红吧?”这种极具灵性的艺术感觉,这种不同艺术形式间的化在一起的借用,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推程玮;在九十年代以后,数韦伶。程玮偏重音乐,尤其是小提琴,韦伶偏重舞蹈、绘画;程玮更多古典的抒情、浪漫,韦伶的绘画中则多少渗进一些现代色彩。她们都因此使自己的小说、散文更舒缓和灵动。
象征也在韦伶的小说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韦伶作品中的象征有多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局部性的、个别性的象征,如《幽秘花园》中的“远方”“蓝石头”等;一种是贯穿性意象的象征,如《幽秘花园》中的花园,整个作品几乎都建立在这个处在中心位置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上。还有一种是整体性象征,即作品中的整个故事作为一个符号系统成为一种隐喻。韦伶作品中最有特色的象征即在这最后的一种。关于这一点,斑马曾有一个很准确的评论。在谈及《出门》这篇小说的艺术表现时,斑马称它是“无技巧痕迹之后的象征”①。所谓“无技巧痕迹之后的象征”,我理解,就是看不出象征的象征,就是作品中具体描写的艺术世界和它隐喻、象征的世界间距离极小,不仔细体味,甚至都感觉、辨别不出来。比如《出门》,可以说是以少女凌子的第一次独自出门象征性地表现女孩第一次独立地走向社会、走向外面的世界的感觉,但后一层意蕴表现得极轻极淡。作者主要关心的是自己具体描写的层次,完全像一般的写实主义小说一样写人物很具体很现实的行动、心理,讲究细节的真实,讲究情节的合理,讲究人物性格的丰富、生动,并不在意用这个人物、故事作为符号去喻指另一些人物、世界。海明威不承认他的《老人与海》是一部象征主义小说,韦伶也未必认为她的《出门》有多强的象征性。同理,《幽秘花园》《红土道》《山鬼之谜》中的象征含义,可能也是读者“读”出来的。但读者能够“读”出来,多少也有他们的依据。两个世界的距离极小,但再小也是一种距离。极淡极远,“无技巧痕迹之后的象征”,这本身也可能就是一种技巧。象征以实写虚,有双重影像。如何处理这双重影像间的距离一直是象征艺术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太近,没有距离,A就是A,当然不成其为象征。但太远,用来象征另一个事物、另一个世界的表象世界没有自己独立的生命,仅仅成为一种符号,成为象征世界的能指,象征形象和象征含义之间的联系非常稳定、单一,象征便向寓言的方向发展,象征艺术特有的朦胧感、空灵感便消失了。于是,问题的关键便在如何把握好这个距离的度,但这儿又无统一的规则可循。只要自身把握准确、描写生动,距离远近均可成功,只是美感的性质有所不同。韦伶的小说,作为一种整体象征,表象世界和意指世界之间的距离小,与写实主义小说较为接近,其空灵是写实主义丰富充实基础上的空灵,其朦胧是其描写对象本身就具有的朦胧。韦伶作品内容上的特点和形式上的特点在这儿再一次统一起来了。
①斑马:《游戏精神与文化基因》,甘肃少儿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