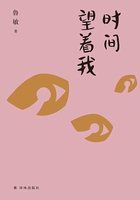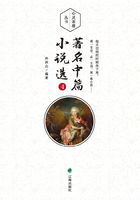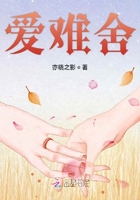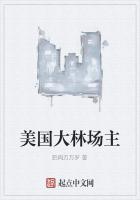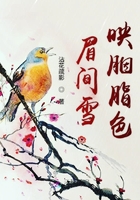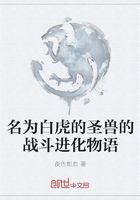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中国文学刚从十年动乱的阴影中走出来。虽然还背负着因袭的重负,但一些重要的改变已在悄悄地发生。在童话创作领域,改变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种在当时被称为“热闹派”的童话的出现。虽然后来人们了解到这类童话并不是什么“新事物”,其不仅仅在西方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就是在中国,三四十年代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等早已将其操练得颇为熟稔。但是,在十年动乱后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还是给人们由于长期的禁锢、闭锁已变得麻木僵化的审美神经带来一阵兴奋,使人们看到在熟悉的政治宣传、道德说教、社会隐喻之外还有一种以怪诞、变形、游戏为重要特征的作品。在这以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这类作品不仅由少变多,历久不衰,而且艺术上不断创新,逐渐形成自己的题材范围、风格类型及相对稳定的创作群体。周锐就是这一创作群体中重要的一员。
谈及“热闹派”童话,人们首先的印象就是作品的形象层面大幅度的变形。首先是故事中的人物、事物及其构成情景等远离生活本身的面貌,给人一种怪诞的感觉。用杜夫海纳在《审美经验现象学》中的说法,就是“现实系数”较小。读者阅读文学作品,一开始就有一种巨大的“身体上”的距离感。周锐童话就有以这种方式创造的艺术形象,如《鸡毛鸭》《阿嗡大夫》一类。但就整体而言,这种变形在周锐童话中并不是最明显。他并不特别多的使用拟人、超人形象,出现在他作品的形象,如《勇敢理发店》《P·P事变》《未来考古记》《挤呀挤》《千年醉》《宋街》等作品中的多是常态的人。周锐童话的怪诞、变形主要表现在作品的情节上。作者常常大幅度地突破人们熟悉的现实生活的逻辑,想落天外,将人们以为无法联系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将人们以为无法分开的东西大距离地分开,构思出一个个新颖别致、含义深远的故事。把握这些构思,把握这些构思的凝定形式即作品的情节结构,就成为我们理解周锐童话首先的切入点。
在周锐较早的作品中,可找出一些最主要的结构作品的方式。
畸联,或曰异体嫁接。这是一种非常态、超常态的组合方式。在现实生活中,在常态性的思维和想象中,每种事物都有我们熟悉的性质、特征,有我们熟悉的与周围世界的联系方式及运动方式,由此构成事物、事件及世界的常态性面貌。如果思维不遵循这些常规,在想象中改变事物的性质、面貌,改变事物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及运行方式,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将这一事物的特征放到彼一事物上,将彼一事物的运动方式放到此一事物上,就会创造出非常态的事物、事件,使世界现出奇异怪诞的面貌来。如在常态中,鸡是鸡,鸭是鸭,鸡毛长在鸡身上,鸭毛长在鸭身上,可在周锐童话中,却出现一只鸡毛鸭,鸡毛长在鸭身上,成为一个异体嫁接的怪诞的形象,对人们的视觉造成强烈的冲击。在常态中,糖是甜的,盐是咸的。但在作者《咸的糖,甜的盐》这篇童话中,事物的性质却发生了错位,糖的性质放到了盐的身上,盐的性质放到了糖的身上,由此在大不留城和小不留城之间引起了一场颇为热闹的混乱。这还是就事物最外在的面貌最一般的特征而言的。如果再进一步,畸联、异体嫁接不是简单地发生在事物最外在的个别特征上而是扩展到牵涉许多事物的事件间,怪异的特征便在世界的深层表现出来。如在生活中,电话线路的连接是有规律的。拨A的电话就打到A那儿,拨B的电话就打到B那儿,要A和说话就拨A的电话,要B和说话就拨B的电话,一切按部就班,井然有序。但如果秩序发生错乱,拨A的电话打到B那儿,或与A通话B也能听到,那该是一种什么状况呢?《电话大串联》就是以想象的方式创造了这样一种假定的状况。A拨通情人的电话,一开口就是一大堆亲密的话,结果电话串线,接听的是他的妻子,于是一场好戏出现了;B给A打电话,大说C的坏话,结果电话串线,他们说的话全被C听到了,这下自然更热闹了。还有《疼痛转移器》。疼痛是一种肌体感觉,肌体感到疼痛是因为受到创伤或发生病变,一般是不可能在不同肌体间随便转移的。如果发生这种转移,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疼痛转移器》构思的亮点就在这个“如果”上。作者利用童话这一文体的特征和自己编故事的权利,将只存在于“如果”中的现象搬到常态的语境中来,结果就生发出常态情景下人们无法看到,甚至无法想象到的出奇景象。畸联不是两个不同事物胡乱相加,在不合逻辑的异体嫁接中,人们创造了一个新事物,揭示、表现了在原来两个事物中都没有的新内容。
时空错位。畸联、异体嫁接一般是指同一时空背景中两个不同的事物、事件的畸形搭配、组合,如果这种畸形搭配、组合主要表现在不同的时空之间,就形成叙事中的时空错位。时空错位联系的不只是两个单一的事物、事件,而是两种不同时间里的生活方式、生存状态,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价值观念,所以很容易引出矛盾、错位等喜剧性情景来,这是周锐喜爱的构思方式,他的童话中有好多篇写得不错的作品就是以这种方式写成的。如《千年醉》,两个明朝人喝了一种叫做千年醉的酒昏昏睡去,在千年之后的今天醒来了。于是,两个穿着明朝的宽大衣服,戴着明朝的高帽子,说着明朝语言,有着明朝价值观念的人来到今天的大街上,自然成为今天人眼中的怪物,和今天人发生一幕幕充满喜剧色彩的矛盾冲突。《千年醉》是将两个古人带入今天的社会,《宋街》则是一批现代人试图进入古代社会。为了吸引游客,人们复制了一条古老的宋街,街道、楼房、物品、人们的穿戴以及语言都模仿宋人,在今天社会的背景上创设了一个古代人的群落。开始,人们争着抢着要住到宋街去,可真的到了宋街,发现什么都不习惯。没有电视、没有电话、没有空调、没有汽车,连话都不知怎么说了。于是人们又急着迁出宋街,回到现实生活的轨道上来。更耐人寻味的还是《未来考古记》。作者以假定的方式将人从现实生活的位置中间离出来,站在未来的时间点上,让未来的考古学家面对一个今人非常熟悉的蜂窝煤,匪夷所思地作出种种智慧的博学的然而注定又是让我们哭笑不得的猜测和考证。还有《从人到猿》《当蚊子成为稀有动物》等,都通过时空错位创造一种特殊的情境,将某种只存在“如果”中的假定以实现了的方式放到眼前来,新奇怪诞让人深省。
换位、颠倒。《森林手记》是一个颇有趣味的故事。一个兽语大学的学生到森林中去捕兽,结果却被野兽们抓住放在栅栏围起的大笼子里供野兽们参观。平时我们见惯了人将野兽抓来放在铁笼子里、放在深坑大池里供人观赏,谁见过野兽将人抓住关起来供野兽们观赏呢?还有《替身日记》。一个人被请去给别人当替身。当替身当然要忘掉自己,把自己变成要替的那个人。被替的人是好人,自己变成好人;被替的人是恶棍,自己也要变成恶棍;被替的人热情奔放,自己要热情奔放;被替的人冷漠寡情,自己也要冷漠寡情。问题的困难还不在能不能扮好别人,而在能不能完全地放弃自己。扮演、换位能给人许多在常态下没有的体味。
简化、省略。颠倒、错位、异体嫁接是改变事物的面貌,如果不改变对象的秩序、排列规则,仅有意识地抽取其某些部分,是否也能改变事物的面貌,使对象显出非世界本身形式的特点呢?回答应是肯定的。历史上许多童话作品,如拉斯别的《敏·希豪生奇遇记》中就有许多成功的例子。在谈及自己的创作时,周锐曾说,写《电话大串线》,“故意不直接描写人物的表情、动作,通篇采用对话,开放听觉,关闭视觉,以给读者留下一块想象的空间,产生一种别致的阅读效果”①。以后,也是出于这种有所开放、有所关闭的想法,他又写下了《站牌与糖葫芦》等作品,通篇只有动作、画面,没有一句对话,仿佛舞台上的哑剧一般。世界本有色彩有画面也有声音,去掉其中任何一项就省略、简化了对象,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转向非世界本身的形式。这还是就世界呈现在不同感官中的印象而言的。就是同一感官中的对象,如视觉,也同样可以出现这种现象。周锐的所有作品几乎都不用背景,没有具体的时间,没有具体的空间,人物没有性格史,人物关系极度简约,像年画、漫画,从具体的世界中抽象出来。严格地说,这也是一个高度省略、简化的世界了。这种构建艺术世界的方法虽不像错位、颠倒一样明显地改变视觉世界的面貌,但实际上比后者更普遍更深刻地影响着周锐童话以假定的形象呈现自身艺术世界的方式。
①周锐:《开放·关闭》,见《周锐童话选》,少年儿童出版社,1994年版,第377页。
突转、扑空。突转、扑空,也是创造新异故事和喜剧效果的一种常用手法。其主要策略就是叙述者有意识地进行误导,然后在某一地方发生突转,让读者扑空,落入作者事先设置的思维陷阱,发现自己上当,成为被取笑的对象。周锐有些童话艺术构思就建立在这种修辞效果上,如《兔子的名片》。兔子因为弱小,常常被欺负,于是想出主意,在名片上拉上一个强有力的“朋友”。遇上狐狸就说自己是狼的朋友,遇到狼就说自己是老虎的朋友,遇到老虎就说自己是大象的朋友。后来真的遇到大象了,再也想不出比大象更有力的角色,只好等着受罚,读者也以为兔子这回真的要倒霉了。可大象既没有向它要名片也没有欺负它,因为大象是不恃强凌弱的。因为怕被欺负而拉上一个强有力的朋友是一种思路;交往中讲友善不恃强凌弱,是另一种思路。当读者在作者的引导下沿着第一种思路顺理成章地向前推进且屡试不爽时,叙述者却突然地跳到另一种思路上,读者按惯性落入思维的陷阱。当他觉悟到时,发现自己已成了被取笑的对象。《小猪12和十二只蚊子》大体也是同一手法。房间里共有12只蚊子。如果房间里只有一个人,12只蚊子可能同时叮他;有两个人,可能摊到的只有6只。以此类推,自然是房间里的人越多越好。这就是作品中小兔、小猪、小羊的思路。可小猴却终止了这种思路:为什么一定要等蚊子咬而不打蚊子呢?从分摊蚊子到消灭蚊子,这是两种不同的思路,叙述者将读者引入第一种思路后又突然地跳出对其进行善意的嘲弄。这是一种思维的游戏,幽默的喜剧中包含着人生的智慧。
归谬。归谬是错误、不合理的相加。在生活中,任何事物都有合理的位置、大小、方向、速度;在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中,也有大致和谐的比例、限度。只是这种比例、限度并不是完全严格的,更不是一成不变的。放在日常的语境中,他们一般并不破坏事物的常态面貌。但是,如果将事物运行及与周围世界联系中的某些不合理因素集中起来,甚至有意识地夸张、放大,或者从原来的语境中抽象出来放到一个能将这种不合理性突出地呈现出来的语境中,就形成归谬。归谬未增添事物的内容却改变了事物的结构,结果仍改变了事物的面貌。比如《勇敢理发店》。勇敢本是一种不错的品质,但它有自身运用的范围和把握上的分寸。离开了这些,或只模仿其表面上的形式,就容易歪曲勇敢的内涵。如果这种歪曲的幅度超出寻常的范围,且不只表现在个别的细节上,事物就会显出怪诞的面貌。过桥不走桥面,而是攀上滑溜的铁栏杆,来回在空中走钢丝,看似勇敢,其实是冒险;夜晚不回家,呆在阴森森的地窖里,看似勇敢,其实是逞能。个个剃光了头还不过瘾,还要拔光头发去充秃头大将军;不光拔光自己的,还要拔别人的,连老爷爷的胡子、女孩子的头发也不放过……经过这么一“归谬”,包含在那种只求形式不讲实际内容中的所谓“勇敢”,其荒谬性就集JQKA中地表现出来了。还有《轮船》,轮船朝什么方向航行,去什么目的地,一切听船长的,这本来就有些荒诞。但如果只发生在某一条船某一个船长身上,这荒诞还不能很明显地表现出来。现在又来了个“机会均等”,每月抓一次牌,谁抓到大王就听谁的。结果第一个月听某个英国人的,他要去日本;第二个月船长换成了日本人,没等船到日本便调转船头去非洲。如此掉来掉去,船永远只在大海上转。小荒谬变成太荒谬,其不合理性集中地、突出地表现出来了。
荒诞、噱头。噱头和荒诞都是对正常的偏离和挑战。如果偏离只发生在较为局部的层次,只为某些喜剧性效果而极度地夸张某个对象而制造某笑料,便是噱头;如果这种偏离和挑战不仅幅度极大,而且延伸到精神层面,使事物整个地失去寻常逻辑,便形成荒诞。比如《爸爸妈妈吵架俱乐部》。一般说,“吵架”和“俱乐部”,是两个绝不兼容的概念,“吵架”而有“俱乐部”就是荒诞。“吵架”不仅有“俱乐部”,且上俱乐部吵架的都是爸爸妈妈,就更加荒诞。还有《P·P事变》。两个小学生在课间为争一张乒乓球桌而发生争吵,这本是一件极小的事。但故事却从这一点生发开去,由小学生引出他们的父母,从其父母引出他们的牌友,牌友引出病友,病友引出拳友,拳友引出钓友,钓友引出咖啡友,咖啡友又引出保安局长,保安局长派出防暴处长,当防暴处长派出50名防暴警察和50名防爆特工跨上摩托车就要冲向学校的时候,小学生却因为上课时间到了而自动地散去,一场“事变”就这么平息了。一场寻常的小学生的矛盾能像多米诺骨牌似的将社会各个层面的人,包括国家的警察、保安部队都调动起来,这显然是荒诞的。作者的另一些作品如《舞蹈型地震》《JQKA轮船》等大致都属于这一类型。
周锐童话中也有一些按常态思维、故事中事况境况无明显变异却同样构思奇巧别开生面的。《一个瞎子和一只不会嗡嗡叫的蚊子》,讲有个瞎子因失去视觉而发展了听觉,练就一种根据声音就能飞快地抓住蚊子的本领。如果仅如此,情节就非常一般,甚至无法成为一篇小说,作者的机智处在于他设计出一只蚊子,也因先天缺陷而不会嗡嗡地叫,因而练就了一种没有声音却能狠狠地叮人的本领,最后让这两个都有缺陷但却因此成就出一种特长的个体相遇,两者都因为怜惜、钦佩对方而不忍互相伤害了。作者近年写成的《黑嘴唇》采用的也是与此相近的方式,负负得正,构思仍有一种出奇制胜的效果。
二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周锐的童话创作出现了一个较大的变化,就是创造一组取材于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以“幽默”为贯穿特征的长篇系列,包括《幽默三国》《幽默水浒》《幽默西游》《幽默红楼》《幽默聊斋》等。由于取材对象和美学追求的变化,作品的艺术构思及表现也显出不同的特点,那就是借景、生发和戏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