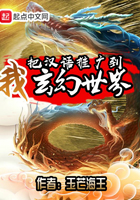贺家湾这年的春节真说得上是热闹非凡了。就像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房屋经历了由草房到瓦房,由瓦房到平房,再由平房到楼房的变化一样,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农村地方文艺也经过了很多变化。不过三十年来的农村房屋是越变越好,而农村地方文艺却是越变越糟糕,地方文化主要靠麻将来支撑。至今老百姓还怀念大集体时期,尽管那个时候人们吃不饱肚子,物质也并不丰富,可那时人们的精神生活却不像现在这样贫乏。那时候正如贺世普现在所回忆的一样,每个大队都建有自己的文艺宣传队,演样板戏,唱革命歌曲,还通过一些自编自演的节目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心工作,以教育群众和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每年到了冬季农闲的时候,都是各大队文艺宣传队排练节目最忙的时候。大年初一,全大队的男女老少都早早集中到了大队操场上,看宣传队的演出。这一天,是所有庄稼人最快乐的一天,那些散发着泥土味的演出,常常让在土里忙了一年的庄稼人开怀大笑。初一演了过后,从初二开始,宣传队就开始到各生产队演出,一般一个大队有八至十个小队,有的年轻人宣传队演到哪儿就跟到哪儿,节目内容都记熟了,台上演员还没把台词说出来,台下的观众就抢着说了,惹得台上台下一片笑声。每个小队巡演完了以后,就开始在各个大队间互相交流演出,一直演到正月十五,公社组织文艺会演,评比出先进大队和优秀演员,进行表彰。
那时,贺家湾的文艺宣传队年年都是先进。除了贺家湾宣传队有多才多艺、能编能导也能演的大才子贺世普以外,还有在全公社演员中都有一定名气的郑彩虹。郑彩虹是当时大队书记、老革命郑锋的侄女,长得十分妩媚可爱。柔媚的眼睛上罩着弯弯的柳眉,明净而白皙的面孔上泛着玫瑰色的光芒。清秀而粉红色的嘴唇,嘴角向上,笑起来既甜蜜又开朗。身材苗条,一根长辫子垂到腰际,不用化妆,就是一个活脱脱的李铁梅的形象。那时很多男青年跟着宣传队一个小队一个队地赶,不是看演出,主要是看郑彩虹——那个舞台上的“小铁梅”。那个舞台上的“小铁梅”只要一开口唱“我家的表叔数不清”,下面必然有很多男青年跟着她的声音唱下句“没有大事不登门”。可以说,那时郑彩虹的“粉丝”丝毫不低于今天那些明星们。郑彩虹后来成为赤脚医生贺万山的妻子。那时万山并不跟着宣传队跑,万山做梦也没想到他能娶上郑彩虹。用后来一些人的评论说:万山是拣了一个漏毽踢。世普编的那些三句半、对口词、快板书、唱词,甚至小剧,一般都是紧密配合当时那些中心工作的。取材都是当地群众所熟知的好人好事,语言也十分通俗,所以不但公社领导很欣赏他,群众也很喜欢他。贺家湾宣传队有了这么两个人,不想当先进都难。
除了宣传队演出以外,20世纪70年代中期,电影也开始在农村普及起来。公社成立了电影放映队,放映员要不是公社领导的子女,就一定是他们的亲戚。放映机是那种十六毫米的小机子,影片也不多,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部。但是和春节看演出一样,电影队来到哪个村,就成了哪个村的盛大节日。一般幕布还没拉起来,家家户户的人便都会端了板凳,从四面八方来到放映的操场上,把地方占好。先来的占的位子,一般都靠近放映机旁边,后来的便只有占到后面。那时,为争位子也会发生一些争吵,但这种争吵会很快消失。在看电影时,一些年轻小伙子趁着人多拥挤,也会搞一点小动作来捉弄女青年,以寻开心。一般的小动作就是把一个靠在女青年旁边站立的“兄弟伙”猛地推过去,让他去撞女青年。女青年有时会被撞一个趔趄,甚至摔倒。也有的时候人太多,站得插麻秆一般,一人被撞倒,哗啦啦会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一大片,那被推倒的女青年被压在下面,锐着嗓子大叫。可“肇事”的男青年却会在一旁假装正经,抿着嘴唇笑。那时不管是大队的操场还是生产队的“晒坝”,都不像现在的水泥地一样平整,要想放平凳子,有时要用木头或石块来垫平凳脚。还有一些小伙子为了捉弄女青年,就把她凳脚下面垫的东西忽然拉掉,然后转身就跑。站在凳子上的女青年往往会摔个四仰八叉,让周围的人一阵大笑。
不过所有这些小动作,都是在电影还没开始放映之前干的。因为电影没开始放映前,头顶灯光明亮,再大胆的小伙子也不敢有太出格的动作。可是一旦电影开始放映,那些敢于“作奸犯科”者就不会再满足让女青年摔个四仰八叉之类的小打小闹了。那些胆大妄为的“坏小子”,会趁周围一片黑暗、女青年专心一意地沉浸在影片的内容中的时候,在她的屁股上摸一把。女青年如果没有被人看见,一般都是不会吭声的。要是被人看见了,便会哭着回家去。然后又会有女青年的同伴跟着去劝,不一会儿,那个被人摸了屁股的女青年又会回到放映场上。与其说是被摸了屁股的女青年是禁不住电影的诱惑,还不如说是处在青春期的女孩,她们本身就有着被异性抚摸的天然渴望。有一回贺家湾放电影,后来做了贺家湾支部书记的贺世忠,就曾经摸过贺桂花的屁股。贺桂花是后来成为被称为村里“四虎”的贺良全、贺良建、贺良礼、贺良毅的姐姐。她当时才十八岁,面孔被阳光晒得黑里透红,有着一个小巧的鼻子和一双圆溜溜逗人喜欢的大眼睛。但因她个子不太高,长得又有些胖,胸部又饱满又突出,更不用说两瓣丰腴而圆润的屁股了。走起路来,两瓣屁股一甩一甩,像是在召唤什么。因而她走到哪里,哪里小伙子的目光便会被她那两瓣屁股给勾走了。她的屁股被贺世忠摸了以后,也像失去了什么宝贵的东西一样哭着离开了电影放映场。但后来贺桂花竟然不但不恨贺世忠对她耍了“流氓”,反而爱上了他。两人悄悄经历了几年的地下恋爱,一个发誓非他不嫁,一个发誓非她不娶。但两人最后还是没有冲破贺家湾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犹如铜墙铁壁一般坚硬的“同姓不通婚”的规矩,没有成为夫妻,留下了一辈子遗憾的事。但在当年贺家湾放电影中,谁也没有胆量去摸郑彩虹的屁股。这一方面的原因固然是因为郑彩虹是支书郑锋的侄女,所以郑彩虹的屁股就犹如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另一方面,也是在所有这些不安分的小伙子心目中,都觉得郑彩虹实在是太高贵、太圣洁了。高贵和圣洁得好比传说中的仙女,这些小伙子只能仰望,而不能有丝毫的亵渎。这些当年发生在电影放映场的风流韵事,它们和电影本身一样精彩,现在回忆起来,既有几分苦涩,也有几分甜蜜。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几年,庄稼到了户,大队宣传队的演员也不能记工分了,大队又没了集体财产,因而这时不管是“李铁梅”还是“杨子荣”,干部们都只好让他们下岗了。至于贺世普围绕中心编的那些三句半、对口词、表演唱,也失去了意义。何况这时贺世普已经调到乡中心校当校长去了。这时他的中心工作,是要完成上级下达的升学任务,而非原来那些写写画画、唱唱跳跳的事了。但在此时,各大队那些由党统一领导的宣传队虽然没有了,但仍然会在春节期间,有一些简单的文娱活动开展,比如耍狮子、逗车幺妹、打连响等。这些活动,有的还是由干部组织的,有的纯粹是民间爱好者自发兴起的。干部组织的,也只是发发号召,提供一些道具和服装(比如原来的锣鼓、衣服等),并不付工资。民间自发组织的更不用说了,他们组织的目的本身就不是为了什么崇高的意义。他们只是觉得在一起做这些事热闹,很好玩。民间便把这些人叫作是“老妖艳”。春节期间,几个“老妖艳”敲锣打鼓地满村串,给家家户户拜年。走到每一家的院子里,先是锣鼓哐才哐才地一阵响,把大人小孩吸引过来后,表演“大头和尚”的便会从随身背的人造革挎包里,掏出一张印有“恭喜发财”四个字的红纸条,过去用胶水贴在主人的大门上,然后挥手示意锣鼓停下来。锣鼓一停,那“大头和尚”便会摘了脸上的“戏脸壳”,朝主人一拱手,就朗声说出一段“四言八句”来:
正月里来是新年,青头狮子来拜年!进门主人脸带笑,又搬板凳又礼貌。从今狮灯耍过后,荣华富贵万万年!
“大头和尚”念毕“四言八句”,锣鼓又是一阵猛敲,狮子或车灯又表演一些节目。这时车灯或狮子表演节目,为的是等待主人拿“利市”。主人自然心领神会,待车灯或狮子表演得差不多了,就会笑吟吟地进屋去,拿出一条烟或一个早已包好的红包递给“大头和尚”。“大头和尚”往往会把红包打开看一下,如果主人给的“利市”多,“大头和尚”马上又会示意锣鼓停下来,接着他又会念上一段:
这个老板很大方,发财就是第一个!打的粮食垒起尖,喂的猪儿大得玄!挣的票儿多得很,修座“洋房子”都用不完!
下面舞狮的、耍车灯的、敲锣打鼓的兄弟伙一听“大头和尚”这话,便明白这主人给的“利市”多,也很高兴,等“大头和尚”的吉利话一完,锣鼓又便马上热烈地响起来。
如遇有那等小气吝啬的主人,锣鼓响了半天,也不见动静,或虽有动静,可拿的“利市”非常微薄,那“大头和尚”便也会唱:
送财送了大半天,不见主人在哪边。有也罢,无也罢,请你主人家答个话。
或:
这个老板很不错,只是“利市”不太多。你把包包摸一摸,再添几块也不多!你把零票子抓一把,儿子儿孙上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