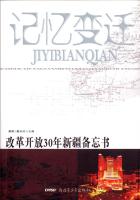第三章那个女鬼,一定认识你
惊悚?由粉红变黑色,这跨度似乎有些大,让他有些难以置信,换了一脸惊讶表情。
对,惊悚!
他猜中了前头,可是却猜不着这结局。
(喷子兄又冒出来了。)
喷:难道,你被女鬼吃了?
答:你丫才被女鬼吃了呢!(噼里啪啦的肉搏声)
(end)
我眼神有些迷离,嘴里喃喃自语,仿佛回到了那个梦境中……
我渐渐地靠近,我左手捏住了柔若无骨惨白似雪的小手,右手准备搂抱她那娇媚无双的身躯。她的背也是出奇的柔软,触手处浑不似有突出骨骼的灵长目动物,倒象是章鱼一般的无脊椎动物。
海妖?吃我?
用美妙的音乐将我勾在身边,再食我肉,饮我血,将我化为一堆了无生气的白骨,再也无法与美女作伴,无法与键盘为伍,无法含饴弄孙取乐,无法与日月同辉!
去******海妖!爱吃不吃!
反正老子活着也不痛快,爱吃不吃,过把瘾就死!有道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男人又臭又硬,整个吞下也不好消化,最好象牛吃草一样,反复的嚼,再反刍的嚼,嚼得碎碎的成了渣,让我成为名副其实的渣男,也利于海妖消化吸收。也算是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客串一把营养师,对眼前这位美丽的动物世界,不,美丽的海妖世界作出的最后贡献。
眼前的湿身绝色丽人,啊不,绝色海妖,在我的手触碰到她背脊的一瞬间,脸上忽然变得很奇怪。她惴惴地紧盯着我的双眼,眼神里透着忐忑,惶恐,又似好奇,又似享受。那神情竟然蜕去了之前的妩媚性感,变得说不出的纯真可爱。这种纯真可爱,绝不是一种熟练的伪装,而是从深藏的骨子里穿透而出,让阅人无数的男人都能不由自主酥遍全身为之倾倒的奇妙滋味。
我心中一震,身下热火袭来,浑身就象野火燎原,要是没有狂风骤雨的忘我洗礼,绝不能得以脱困。
我用力地将她拢到身前,俯下头,在她温润如水的唇上奋力一吻。
这一吻,情定三世浑不觉;
这一吻,海枯石烂不负约;
这一吻,粉身碎骨灯不灭。
她在手足失措,在诚惶诚恐中承受了这一吻,随后,索性闭上了眼睛,放松了软玉般的身体,坦然面对我疾如风暴狂似怒涛的这一吻。
可是,好景不长。正在我们彼此陶醉在桃花幻梦中之时,眼前突然金光四射,耳中听到一声巨响,随后身旁的水中浪花四溅,旋涡翻滚。她也猛然从激吻的沉醉中惊醒,一把推开我,但一双美目仍然恋恋不舍地落在我的脸上。然后,整个人身如同最后时刻的泰坦尼克号,飞快地沉入水中,连一根黑丝一片粉纱都不见。
金光转瞬而逝,眼前一片黑暗。我茫然若失,怅然四顾,四下里一片死寂。没有光线,没有声响。
我分不清自己究竟是在河中,还是在海上。只知道自己杵在水中,不浮也不沉。
还我吻来!
海妖来吃我!
我大声地喊叫,试图掩饰我的惊悚,我的恐惧,我的无奈。
什么声音?
我猛然听到耳边再次响起哗哗的水声。汩汩的水花涌起,被什么东西搅动着,又翻腾着旋进水中。
是海妖吗?
她回了?
那一抹抹抹不开的嫣红。
老虎?狐妖?海妖?
男人通通不惧怕这些,因为,男人是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中间部位没有脑回路,从不打脑子过……
这时,世界渐渐通明起来,我眼中渐渐开始视物,见到不远处的水中央又是黑丝涌动,上浮,露出一个少女的头部。却是一头齐颈短发,容貌却完全不似先前的海妖,也不象她那般成熟又矜持,有种女人的独特韵味。但是,从肩上露出的粉色蕾丝却是如此的熟悉,分明就是先前海妖所穿纱裙。
这少女很稚嫩,一脸清秀,满眼惊恐。
她的面相依稀在哪儿见过,而且似乎是曾经时常见到的人,但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想不起来她是谁,想不起来曾经一起经历的苦痛悲伤,一起享受的快乐时光。
哥做事时记性很差,但记人长相却是一流,即使仅有一面之缘的人十多年后偶遇也能一眼认清,说出来龙去脉。象今天这样的断片和茫然,完全不是哥的一贯风格,这让哥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还没到三十,就老年痴呆了?
哥竟然不明觉厉就忘掉了一个人。
少女。
当我正在感怀我未来的幸福指数时,少女突然象失去了水底的支撑,在水中载沉载浮,不时咕嘟地喝上口水,然后手足无措地看着我,厉声高喊着“救命!救命啊!”
我立刻惊醒,双手立刻拨动水流,一个猛子扎了过去,等我出水时,离她仅有一手之遥。看着她在水中拼命挣扎的满脸恐慌之色,我的心里猛地一悸,渐渐地,心痛的感觉四下扩散,让我毫不犹豫地伸出右手,一把抓紧她的手,将她带离出水面,并且,一边轻拍着她的后背,一边轻声地在她面前呢喃说着“乖,乖,别怕!别怕啊!”那神情,那语气,无比地爱怜,无比地宠溺,就象在哄一个即将睡去的婴童。
少女不再惊恐,不再无助,脸上的纹路也变得越来越柔和,越来越甜蜜,越来越感动,仿佛已经完全从溺水中走了出来,重新开始被噩运打断的生命。
我突然心中一阵冲动,看着她似乎已经恢复了生机的俏脸,急切地问一句。
“你是谁?”
这句问话似乎象一只闷棍击在她的后脑,令她猛然一怔,痴痴地看着我。与此同时,脸上的表情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狰狞,好象我这句问话是滑天下之大稽一般。
我的心中没来由的一凛,似乎在质问自己,为什么会问这么愚蠢的问题。
接着,我就看到了我二十多年人生旅程中最让人惊悚的画面,即使是在梦中,也让我癫狂得无法自已。我敢说,几年前小舅死时,我近距离看着他面目苍白毫无血色的遗体慢慢推入焚化炉中烧灼时,都不如这场梦境令人魂耗魄丧。
她的脸皮以一种极快的速度脱落,随流水而逝,紧接着的是脸上的肌肉,一边糜烂,一边翻涌,一边掉落,一边流走。很快的,一只石灰一样白色的头颅出现在我的眼前,而我的右手,握着的也是一只只有骨节的白骨手。
我内心已经走到了崩溃的悬崖绝壁,假若再多增加一丝恐怖,就会立时晕倒。但我的四肢却丝毫不听使唤,似乎还想抱紧眼前的这具骷髅少女,仿佛抱着的是自己无比重要的爱人,或者,亲人。
我拼命地叫唤,死拼地号泣,我要离开这个梦境,我要回到现实,我明天还要上班,我还年轻,以后还要找老婆,结婚生子,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我不要被吓死!
可我无论怎么呼喊,却仍然没有从梦中惊醒,没有逃离这场恐怖的梦境。
更令我绝望地是,那只头颅空洞的双眼死盯住我,下巴还在一张一合,而且,那一张一合居然还能不可思议地在她那四处透风的光板牙齿间发出来出奇连贯出奇好音质的中国好声音!
“你来晚了!”
这声音竟然象在山谷中高声呼喊一般,幽深激扬,震荡回环。而我,面如土灰,象中了西洋童话里女巫的魔咒,不停地在我脑中来回地发出嗡鸣声,和那句该死的“你来晚了”!
“你来晚了”!
“你来晚了”!
“你来晚了”!
“你妈才来晚了!”我崩溃了,气急败坏地回了句嘴。
少女,啊不,头颅,似乎听了我的回嘴,出离愤怒,突然象病发的癫痫患者一样不停地筛抖,前后左右摇晃。猛然地,头颅从头顶天灵盖裂开一条大缝,然后,两条,三条……
最后,砰然爆炸,粉灰四溅,白尘飞扬。
然后,我望向水中,涟漪中依稀出现了一个我的倒影,象一个西洋大师新刻的大理石雕像,又象一只新生的千年白骨精!
我恐惧地乱叫,但我依然没有醒过来。
看着我虽然不在当时的梦中却依旧看起来狰狞的面目,听着我虽然是小心模拟却也十足恐怖的叫声,天阔不由自主地惊得目瞪口呆。
半晌,他才勉强挤了句,春梦变成惊梦,哥们儿你也太腹黑了!我看你是想老婆想得对世界绝望了吧!
我啐了他一口,骂到,一天早同你倾下解,你想做乜嘢?
你别山东的驴子学马叫了,想我给你解梦,求我呀!他挂着一幅死乞白赖的欠扁相说。
你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了!周公解梦?你会吗?我嘲讽说。
奇了怪了!那跟我叽叽歪歪半天,不是想我解梦是做什么?他偏了偏头,奇道。
我,只不过说出来舒服些罢了。一个普通人再正常不过的噩梦而已,谁指望你解什么鬼梦啊!我可不信他会什么解梦大法,认识他这么多年,除了见他热衷于码阿波吃的,可没见他有这方面的异能。
鬼梦?他猛地一怔,惊呼了一声,若有所思了片刻,一本正经地说,你没说错,我还就真的会解鬼梦呢!
你就吹吧!可劲地吹吧!我对他的吹牛大法嗤之以鼻。
我告诉你,那个女鬼,一定认识你!他居然顶着一张僵尸脸吓唬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