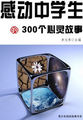"他走的时候,刚刚九岁,与你们一般大......"老祖母轻声说。
"不是普通的九岁,""长颈鹿老爸"接腔,"是重如泰山的九岁!"
老祖母含着泪,笑了。
奕奕从碗橱里取出了加菲碗,搁到自己面前,众人举杯,他捧起碗,贴在面颊边,低声说:"我是洋葱头的孩子,从此以后,你就是我的碗。等到寒假过完,我会带你到城里,去我的家,我们天天在一起--告诉我,你愿意成为'奕奕的碗'吗?"
加菲碗默无声息,而在大人们推杯换盏的喧闹声里,恍惚间,加菲碗发出了欢欣的笑声,奕奕听得很真切,那是加菲碗特有的笑,爽脆中有些不连贯的抖动,像是动听的竹筒琴声。
屋子里人影幢幢,亲戚们会聚一堂,就连大姑的儿子都特地从英国赶了回来。唐叔叔和郭阿姨也携着儿女来给老祖母拜年,那几个小家伙刚过婴儿期不久,有着肥白如藕的手臂、晶莹的眼睛,一见着吃食就走不动路。奕奕和豌豆妹妹心甘情愿地摆出了大哥哥大姐姐的谱,给他们喂吃喂喝。即使小家伙一不当心,把唾沫、菜渍抹到豌豆妹妹的新衣服上,豌豆妹妹也是慷慨大度地擦掉就是,不怒不恼。
口水滴答的当然少不了笨笨,在桌子底下穿梭往复还嫌不够,奕奕一块排骨进了口,它在一旁汪汪狂叫,甚至做出抢劫的前奏。奕奕被它的利牙吓得不轻,情急之下,只得装酷,一副大人不计小人过的姿态,将肉骨头拱手让给它。
老祖母端出一罐亲手酿制的桂花酒,甜香怡人,奕奕和豌豆妹妹被破例批准品尝了一小杯,笨笨急得把前爪搭在了老祖母的腿上,于是,它也分到了一大口。
"这一道菜,叫独占鳌头,"大姑挟起两块鲢鱼头,分给奕奕和豌豆妹妹,"你俩多吃点,往后在学习中可要独占鳌头!"
"那是豌豆妹妹的强项,我是没戏的!"奕奕自嘲道。
一桌的人都笑开了。
"这小子,怎么开窍了,什么时候也变得幽默了?"大姑拧了拧奕奕的耳朵。
孩子们吃得撑了,嘻嘻哈哈地追逐、玩闹,大人们却酒兴正酣。奕奕和豌豆妹妹被安排剥花生、嗑葵瓜子儿,老祖母解释道:"咱们青枣村的风俗,来年的日子兴旺不兴旺,全看这满地的瓜壳了。"奕奕和豌豆妹妹负责任地使劲嗑,扔得一地都是。老祖母不由得喜笑颜开。
酒过三巡,屋外响起了鞭炮声,先是零零落落,逐渐地,声响密集起来。
"我们也该放炮仗了!"大姑说。
一家人拥到门外,在田畦边点燃了烟花。烟花在半空中徐徐绽放,又迅疾陨落,刹那的美,让人目眩神迷。大姑看了看手表,说:"快到零点了,我们都闭上眼睛,虔诚地许下新年的希冀吧。"
大家阖上双眼,在心里默默许愿。
"小家伙,你的愿望是什么?""长颈鹿老爸"悄悄问奕奕。
"说出来就不灵验了!"奕奕诡秘地一笑,拒绝透露。其实,他许下的愿望是,像豌豆妹妹那样,申请一个专属的博客,写好那篇名叫"我的小叔叔洋葱头"的日记,放到自己的博客里,在网络的江湖塑造一个文笔超群的光辉形象。
"老祖母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长颈鹿老爸"搂着奕奕的肩膀,坦白说,"老爸的心愿是,劝说老祖母,请她重新跟着我们回到城里生活。奕奕,这件事,你肯帮老爸吗?"
"没问题!"奕奕与"长颈鹿老爸"击掌为誓。
谁家的电视里传来了倒计时的数秒声,10、9、8、7、6、5、4、3、2、1,咚、咚、咚,钟声敲响了,万炮齐鸣、万众欢腾。
新的一年来临了。
第十一章 后记我在很小的时候,用过一只蓝花瓷碗。深蓝色的镶边,微蓝色的碎花,清淡、朴素,在当时,它是极普通的餐具,但是,我极宠爱它。是那种小孩子的、无原由的宠与爱。我用它吃蒸蛋,用它喝牛奶。我会咕咕唧唧地对它讲话。我霸占它,把它叫做"我的碗"。
突然有一天,这只碗不见了,遍寻无获。它是走失了吗,还是不肯与渐渐长大的我相认?我不明白。
后来,它就一直住在我的心里。
在八九岁的时候,我写诗,写古体诗,分不清平仄对仗。写完,给一个小小"闺蜜"欣赏,此后秘而不宣。那时候,没有写到我的蓝花瓷碗。
十来岁的时候,我写校园小说,也是没有章法没有规矩的,写完,给另外一个小小"闺蜜"欣赏,依然秘而不宣。依然没有提到我的蓝花瓷碗。
我在初中时正式发表作品。自那时起始,在纸笺上,慎重地、严谨地、沉慢地落墨,并且长久坚持下去。直到前两年,在网络里,遇见一些老读者。无一例外地,她们提到我少女时期的文章。爱,哀愁,聚,别离,淡淡的惆怅,遥远的遥远的往昔。一个叫做五月的广州读者,在我的博客留言:一颗颗无声无色的文字,经过你的手,就成了一部影像,流动的画面,安静的声音,震动的内心,你给我们的美,也是最不容拒绝的。然而,在那些震撼了别人的作品中,有灵魂的寂夜,有失爱的寒冷,唯独没有我的蓝花瓷碗。
2009年夏天,写完第十部长篇小说,在成人世界的刀光剑影里纠缠着,无端端地觉得疲惫,我对自己说:我要有一些改变。于是,我想到了我的蓝花瓷碗。我决定写一只碗的故事。一个孩子心里住着一只碗。一只碗心里也住着的一个孩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曾经有过这样的一只碗,抑或一件玩偶、一只球拍、一本书。在成长的路径上,我们往往在不经意间丢失了、遗忘了它们,可是,在被我们百般疼惜过的碗(玩偶、球拍、书)的心里,也许与它们相亲相爱的我们,是永恒的、唯一的,是纵然千山万水都不能够阻隔的惦念。
这就是"加菲碗"和"洋葱头",他们彼此是对方最心爱的宝贝,彼此停留在对方心灵最柔软最纯净的地方。
而奕奕和豌豆妹妹,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相同的是,他们都不完美,不是我们理想中的乖孩子。
在以身高、拳脚、勇气论英雄的小男孩的世界里,奕奕无疑是赢弱的,他不够优秀,不够顽皮,因为温吞而被忽略。但是,他阅读,他思考,他的脑子里承载着许许多多有趣的念头。我喜欢他。
豌豆妹妹是可爱的,是耀眼的,她的学习成绩很棒,是"三道杠",又有一张跟芭比娃娃一样美丽的小脸。不过,她不是微缩版的淑女,她不斯文,没有心计,她伶牙俐齿,淘气得要命,迷糊得要命。我喜欢她。
这两个孩子,有一个相似的特质,那就是善良。他们纯善,他们热忱,他们清澈。私底下,其实我是有贪念的,假如将来,我有孩子,男孩子,要像奕奕那样,女孩子,要像豌豆妹妹那样。
至于老祖母的厨房,那是我自幼所向往的意象。在广袤的乡村,在窸窣作响的竹林侧,在一幢泥与砖头修葺的祖屋里,是新年的厨房,柴火温暖,酥肉喷香,大黄狗慵懒地依偎在老祖母的脚边,一两只小鼠在墙角且行且停......老祖母的厨房--一个听传说、偷嘴的好地方。
我没有在爷爷奶奶身边生活过,而我的外公很早就病逝了。我的年迈的外婆,断断续续地看护着幼年的我。我出生的时候,我的外婆已经接近八十岁,我还没有长成,我的外婆就离世了。
但是,我记得外婆早年在城市楼房的空地间开辟的菜圃。藤蔓上结着黄瓜丝瓜,地面生长着青葱蒜苗,地底埋伏着红薯花生,菜圃里有蝴蝶,有蚂蚱,有蜻蜓。我记得,外婆的厨房,干净、阴凉,她用面粉裹的"麻花",漂浮在肉丸汤里。我记得,阳光和煦的午后,外婆牵着午睡刚醒的我,在小吃店里,为我买甜软的饼,我吃着饼,外婆注视我的眼神温柔而静默......爱恋丰盛的童年,大多数人曾经或正在经历。
可是,谁能在风中久留?谁能从私人纪念碑的浮雕上走下来,被簇拥,被纪念,被传诵?这些孩子,这些物件,大都庸庸碌碌,是历史长河中的匿名者,从没有被光彩和荣耀所眷恋,也没有被耻辱和罪恶的标志所铭刻,处在各种典籍之外,被时光的巨大黑洞所吞噬,悄无声息地消失掉。除非,被书写。于是,我记录它们。静寂的幽微的岁月,宽阔的细渺的忧欢。在字句的缝隙里,它们得以熠熠生辉。蒙田告诉我们,最美好的人生就是向合情合理的普通样板看齐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是有序的,但是没有奇迹,也不荒唐。不过,他忘记了,爱,原本就是奇迹,这虚无持久的力量,宛如一棵树与另外一棵树相爱竞夜之后,在早晨,生出一地蘑菇、野花、木耳,以及在梦境里微微晃动的青草--那真是我们平庸生命的最绚烂的蜃景。真实的怀念与虚幻的构想,就在这间老祖母的厨房里展开,在这里,有我丢失的蓝花瓷碗,有坚守的爱,有不倦的等待,有一段神秘的、古老的故事轻手轻脚地徐徐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