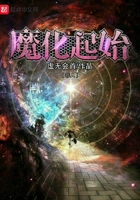倏然。天变脸。从窗口望出去,开始下雨,是通透铮亮的雨,迅猛的,干干的,隔着窗子,也闻到了泥地散发的腥香而燥热气息。这是闷热教人困意渐起的夏季投影,也是青春不响亮却绝对有种的绕梁余音。
他觉得自己摇身一变,成了这场声势浩大雨阵中的微微一滴,与千万个兄弟姐妹一起手拉着手,由九天之上快意刺落,面无表情地直直冲向大地。大地并没有张开怀抱,迎接他们的,是一脸呆板的刚硬,刚硬里起伏着黑,雨淋不透的黑,与她看着自己的,眸中的黑一样,像是性格暴躁的裁缝,不讲手法,把一块琉璃黑,给强塞了进去。其实少女的眼睛,应该软凉一些。
少女蜷缩成一团,化当初在子宫未见天日形状。她眼睛里倒映雨阵凶急,天雷滚滚,每一声都很沉,缓缓发力。每一道闪电憋足了劲道,好似要把这盏天给炸裂开来。天地面目,忽隐忽现。归于混沌。能听见海也在咆哮,它被一根绳子捆绑在地板下,奋力挣扎,困兽犹斗。
他觉得一股微型的飓风立在肚皮,将体内的热力,全吸了去,颤抖,同时,窗口那盘兰花泣开一粒,狂风骤雨,岁月独自流丽。
赤裸相对,四目胶着,谁都不敢把目光下移一点。似脸上筑起了栅栏。他们被对方浓浓眼色包围。房间里有一面镜子,照见刚才电光石火间发生,他的手像是镰刀,喘气的蛮力的刀,不讲刀法,胡乱地砍杀,只为了将藤蔓一般缠绕在她身上的衣服扯下来。于是她的身体得以再见光,光点亮了她,比新雪还白还嫩的肌肤。大气都不敢喘,怕吹破了这绸缎肌肤,她所有毛孔都眯起了眼睛,她的毛孔都是柳叶眉,双眼皮。好看。他的手,在她身上游走,来来回回,无处驻足。像是海翻转到天上再倾下来,雨太凶猛,手指因为极度兴奋,抖动不已,不敢用手掌心去熨平她的不安,只能用指尖,指尖流淌,她的皮肤像是键盘,被触及到的地方无一不跳跃起来,好像之前千万年死寂,只为了这一瞬的重生。狠狠地,放纵地,呼吸生的灿烂。
他着火了。
窗外的疯雨,床下的海浪,都扑不灭这团势猛,奋力,狂躁的火。从头到脚烧了一遍。野草烧尽,她是微热的新土,埋着千万颗弓身待发的种子,蠢蠢欲动。窗口那棵柳树,在断续的闪电中面目狰狞,须条全部翻飞到半空,张牙,舞爪。
她闭上了眼睛。时空也被烧坏了,小时候的记忆无比清晰地窜进脑海,那时候还住在乡下,时间的马达漏油,走得很慢,她常常看晚霞,烧在矮矮的那座山头,火光漫天。窗外是在下火,干柴在火苗中噼里啪啦作响。有一把——愤怒的剑,将云朵剁成一块一块,全部掉落下来。沉重,热烈地,摔落下来。
他们之间,谁是谁的桥,人生是一条苍茫的河,互相搀扶着过,弱水三千,无能载舟,只能从彼此身体卸下一块肋骨来,造船,起航,从此分道,擦肩而过,不顾前世几千次回头。彼岸,花开。开得很蛮。狠狠地。他们一路至此,已是满腔愤恨,就烧成灰烬吧。
雷鸣。更让两人间的沉默显得突兀。语言再花哨,也是苍白,有什么用,身体是最好的语言,又是画笔,又是画板,落笔,一笔,成谶。
一道电,引得那柳树冒出阵阵青烟,火苗抓着雨条窜到半空,迅速被大雨扑灭。他就是在这个时候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漂亮的句号。震耳欲聋,巧夺天工,他把她变成了一个女人,至少不再是一个女孩。
他的目光落在她脸上,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哭的。脸上是斑斑的泪水。
“是因为太痛了吗?”
她半响,才幽幽回了一句:“可是唐木,你不是不能与女生,那个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