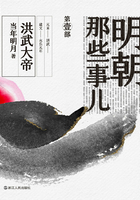“啊……”我恐惧的痛呼,(变成液体后的我)终于懂得了害怕!当时的头皮都炸麻了。
汗毛倒竖的我转身想走(几乎忘记了他就在我的背后),又“唰!”的一声,后腰被狠狠一斧,下肢几乎残了一样不听使唤。真的痛啊!这种伤,这种痛,切肤之痛,痛入骨髓。极大的痛楚就像极大的恐惧一样包围着我。可我是尹诺那种忍者神龟(超强的忍耐力和过硬的心里素质)吗?怕死?!就疯了挥拳肘击,不像样的挣扎。跑不了了,盲拳都能打死老师傅。含恨回身肘击,双龙出海,全身细胞紊乱,身体接连炸裂复又重组,最后甚至和他对A。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揍他个兔娘养的。
心里发狠下手就黑,干得漂亮,我实是黔驴技穷了。你来我往两三下。他还没被我揍成什么样,我身上被他劈过的每一道口子却都在流血(流失体内的液体)啊!
我被割开的伤口都在火辣辣的疼痛,他的每一斧头砍在我身上就是一道口子,我情急骇怕乱打一通,他闷声挥斧和我站撸。伤口加深,流血叠加,被剜去的液体像死蛇一样落地无息,使我愈发矮小,虚弱(他则显得越加高大)……把我仅有的可怜的丁点对抗意识都给彻底捻灭了(这都在变相的加深我内心的恐惧)。
徳莱厄斯杀人如杀鸡一般的放血,我受不了,我崩溃了。赶紧逃吧!管他三七二十一,顶着伤害任他殴,双手赶紧插地掘屁股,拉直了腰板,蓄力在双臂,头往后仰时,就瞧见诺克萨斯之手的脸就贴在我眼前,四目相对,毫毛都看见了,更别说他一扯僵脸的恶笑。
我脸色惨白,心里咯噔一声,仿佛接又漏跳一拍。我太能在这个渗人的表情上看出各种解读了。我脚立马离地,绷紧的前臂把我推送出膛。此时不跑,更待何时。感受着与上一次起飞时大相径庭的紧迫,呼啸的风声在我耳边唱响——这绝不是我因飞行太快而在耳边产生的音爆——而是一道棍子横空出世狠狠的抽打在我的肋骨处,棍子的前端连接着一弯黝黑呈亮的斧板,就横亘在我的腰间,一把把我给拉了回去。
啊!在眼前看着即将要在近身的远处,远了。身后一个狠狠的撞在一片钢铁甲胄上,我还没来得及对疼痛做出反应,几乎就意识到了将要发生的事情,尽管如此,可事实却仍以远远超出我所能想象的秒杀性结束(这个令我震慑的瞬间):我被无情铁手拉回徳莱厄斯身前又是狠狠一斧,结果在我的眼前,诺克萨斯之手浑身一下爆出了血雾,血腥厉吼中他仿佛一个浴血魔神,高高跃起,以不可匹敌的态势,斧起,头落。
在这之后的一秒,我才意识到我的头离开了我的身体。随之跌落,我眼前逐渐失去的所有的视觉,听觉,一切一切……!
以至卡琳,我只来得及向她看了一眼,卡琳也在看向我,她那萎靡不振的脸庞上复又焕发起的容光,向我欢笑。
……
色字头上一把刀啊!现在的我坐在大巴车里,看着窗外的夕阳西下,心里莫名其妙的涌生出许多的感概和难过。
身旁的伟佳和车里的人一半多都睡着了,少数醒着的也在无所事事的发呆,长时间的枯坐,都已经没有了出发时的兴头了。估计车里的人,连同整个车队也只有我一个人会怀抱着伤感看着夕阳。
我还是挺喜欢卡琳的。在每一个寂寞的夜晚,就像许多的男吊丝们一样,我们都在意识中相会,蛤蟆般仰卧在床边。只是伴随着年龄的增长,每次‘开心’过后,我都会有一种失落,(我很肮脏吧?有时我也觉得自己不堪,****,精虫上脑,下流下贱,可一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更觉无所事事,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爱,但每次想起她时,我都会很开心。尤其是这段霸王硬上弓,在惨痛的艾欧尼亚战争回忆中,这是令我时常想起,并常常感到高兴的事情。
我知道我的心态不对,但我已正确的认识到事情本身的错误,并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和检讨:在这件事中,我扮演的是一个草菅人命、巧取豪夺、纨绔卑劣、********,语无伦次的社会败类。在往后的生涯中,我要摒弃这种种恶习,坚决、彻底的与黑暗人性做斗争,和光明、友爱和幸福的人生携手并进,做一个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人!……
这曾经是一份我写给我父母的一份检讨。当然不止这么短。但现在它就是我在开心、难过、感慨、兴奋……之余用来推进情感的增稠剂。
我在车里,看着窗外的夕阳,低低又痴痴的说,“啊!那是东方,卡琳就是太阳!——起来吧,美丽的太阳,赶走那妒忌的月亮。她因她的女弟子比她美丽得多,已经气得面色苍白。既然她这样的嫉妒着你,你就不要再忠于她吧;脱下她给你的这一身惨绿色的贞女的道服,它是只配给愚人穿的。那是我的意中人,啊!那是我的爱。唉,但愿你知道我在爱着你!你欲言又止,可是你的眼睛已道出了你的心事。”我眉眼含笑的看着窗外的夕阳,把它当成卡琳,“卡琳啊卡琳,为什么偏偏是卡琳,否认你的父亲,抛弃你的姓名吧!也许你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只要你宣誓做我的爱人,那我也不愿姓爱因斯坦。”
我好开心呐!
——这就是爱吧,这就是青春期的萌动吧!这种遐想时常让我感到愉悦,卡琳哟!
我回眸瞄了一眼,却正瞧见董德标看我的眼睛立马飘忽向别处。我的脸立马就冷了下来。你个王八直娘贼,吃碗底反碗面的也就算了,你盯着我看是什么意思?做贼心虚的还有好意?……我越恶毒的猜想越觉得心情大坏,连刚刚幻想出的美好意境都被他给败坏了。
我冷冷的用眼睛搁他,隔应他,就像刚才我冥冥之中有所感应的回眸。结果,他倒是沉得住气,愣是从那不再往后看。
很快,夕阳西下。大巴接连使到休息站,“嗤~卟”停车。开门。董德标站起,回身,眼睛不做停留的一扫,拍手,“同学们,下车,吃饭去。”说完,回身,下车,走人。
我甩着一张谁看谁不爽的臭脸,直把班主任给看到下车去,也没见他的眼睛在我身上停留过。
“扎克,扎克,走吧!”
“嗯!”伟佳叫我,正甩脸子的我回头跟他下了车。作为独特的‘祖安的无定形战斗体’的我,既是被创造,又无法再被制造的唯一特殊性,使我倍受有心人的瞩目和监视,保护与争夺。在祖安政府安排下的学生生活中,有时我也感到(并发现)自己身边充斥着各种暗中监视,刻意安排,(即便我现在远离了祖安,这个名义上给予我保护的国家)我也依旧对他人的莫名注视感到反感。
现在身处于人流穿梭的休息站,我也没有那种沧海一粟——麦粒掉进太平洋的感觉,反而带着严重的隔阂感,区分出自己和他人。从各处来的大巴停满了整个休息站。但和我有关系的也就伟佳一个人,他默默无声的走着,我也默默无声的跟着。有时候我挺喜欢这样的沉默,有时候又不喜欢,不想要这样的沉默,这太安静以至于太无所事事了,我只能寄托于精神上的胡思乱想来打发这无聊的时间——唉!这寂寥又平淡无奇的友情啊!
我再次看向天边的夕阳,可惜夕阳已下山,只有正在消退的漫天红云,朝霞晚迟暮,行单终影只。哀叹我郁郁的心情感觉更加寂寥了。
“唉,卡琳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