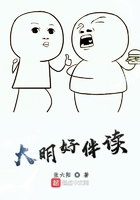二 梁倩呼啸席卷而去,梁安拔腿狂啸追出。一个声若长空哀鸣,一个犹如猛兽逐禽,梁氏兄妹俩一前一后,排山倒海式的呼吼,惊起了一街人。他们跑过梁福记店前,正在守店的李秋霜,听到呐喊紧张地跳到街边,她看到了昂天悲号的梁倩,伸手去拦,大声吼道:“怎么回事?” 梁倩犹如逃命般的慌不择路,一闪而过,朝前继续狂奔。梁安喘着大气,从后面追上,吼道:“妈,把她拦住。”李秋霜愣头愣脑,还不明白怎么回事,梁安也停不住步的向前追去。 李秋霜突然回神,如老母鸡一蹦三跳高地吼道:“梁安,你给我站住!”话没落地,她也长啸追去。 一股巨大的无比悲愤的力量,冲击着梁倩的心胸,迅速输灌全身,让她脚下生风。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天即崩地将陷的悲情,她仿佛发了疯,着了魔,丧失了理性,迷失了方向,被一种什么东西带着她向前飞奔。不仅梁倩感觉自己在飞,梁安也感觉她飞,李秋霜也感觉她在飞,一街疑惑的目光,也感觉追不上她飞翔的翅膀。 梁倩飞出大街,本能的向得胜沙方向疾奔,可到了门口,脑门仿佛又被人一拍,转向海田河,折向水巷口街,然后拐回大街。
大街那些刚刚还没回神过的邻居街坊,还正在议论纷纷,又只见梁倩卷着一股强大的风速,向他们疾冲而来。众人惊心动魄,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紧接着,梁安像一只被风拖着的破了边角的风筝,也随后追来。众人再朝后望,望见李秋霜跌跌撞撞,哭哭啼啼,像要断气折腿的似尾随而上。 替梁氏煮饭烧菜的老妈子,刚买菜回来,正在开门,梁倩一阵风的卷过,扑的打开了门,冲去了,踢开了房门,疲软的倒在床上,无助的嘶着。老妈子还没回过神,又见梁安冲来,她又愣了一下,本能朝后看,看见了李秋霜蹲在离梁宅不远的地上,捂着胸口无声的流着眼泪。 老妈子慌张跑去扶起李秋霜,李秋霜两腿哆嗦,撑了半天都半不起来。歇息了好会儿,她在老妈子的搀扶在,一拐一拐的回到梁宅。进了院子,看见梁安在打门,梁倩紧闭不出,在里面胡乱摔打东西。 李秋霜浑身颤抖,遥远梁安,喘着大气吼道:“你,过来。” 梁安如丧家之犬,灰溜溜地走过来。李秋霜话也不问,扬手啪一声响亮的朝梁安脸上甩了一巴掌,歇斯底里地叫道:“你给我滚!” 梁安被打得晕头转向,金星直冒,老妈子连忙拽住李秋霜的双手,叫道:“别动气,有话慢慢说。
”老妈子一边叫说,一边向梁安打眼色,梁安脸上青紫不分,死气沉沉,满腔委屈的望着李秋霜一眼,低头疾走出去了。 李秋霜像泄了气的瘟鸡,一下子瘫软于地,放声号啕大哭:“梁福啊,你为什么死得这么早,我命好苦哪!” 这时,梁倩闻声出来,扑到李秋霜面前,抱起阿妈,一边哭一边叫:“阿妈,你快起来。”李秋霜抱着梁倩,像溺水鬼抱住了浮板,紧抓不放,梁倩又是一顿心酸,母女俩一个青脸,一个红脸,没来由的抱头痛哭。 梁氏宅院的凄惨嚎叫,引起一街街坊纷纷猜测,又猜测纷纷,为大街这个史上奇闻怪见,争得耳红面赤,却没有一个终极结论。他们有时间争辩,却没时间管闲事,唯有张春堞和刘财来是例外,他们闻风而动,慌张出门,要去问个究竟。 正当张春堞和刘财来匆忙跑进梁氏宅院的时候,何牧人和汪兴正好出现在公司门口。这时,有一个男员工见何牧人回来,慌忙跑出来,说道:“老板,刚才梁小姐……” 何牧人和汪兴都心头顿惊,何牧人连忙说道:“发生了什么事?” 那男员工咕噜吴了一口水,神色紧张地说道:“刚刚梁小姐一路飞奔哭嚎,梁公子紧追她不放,梁母也追着她,他们绕了几条街互相追逐,有人说梁小姐疯了。
” “疯了?”俩个大男人齐叫了起来。 男员工更加慌张了,哆嗦着说道:“我也没亲眼看见,是有人看见,跑来告诉我,叫我转告您的。” “她人在哪里?”何牧人急忙问道。 那员工又说道:“听说都回去了。” 汪兴也惊慌说道:“大哥,我跟你去看看。” 何牧人连忙制止,说道:“公司还有一大堆事要处理,你忙活去,我自己去。”说完,何牧人疾跑出了得胜沙。 梁氏死人般悲天号地的叫声,已经平息。梁倩母女和刘财来夫妇,围着一张桌子,面对静坐,不发一语。突的听见啷当一声响,虚掩的梁宅大门被人猛的推开,冲进了一个人。 众人目光都唰的望向大门,顿时惊呆了。来人竟然是何牧人。 何牧人于大厅门口处,喘着粗气立住不动了。他慌里慌张地望着四人,四人也慌里慌张地望着他,每个人的脸色都不一样。何牧人沉重,梁倩悲凉,梁母惊诧,刘财来阴沉,张春堞冷笑。 “发生了什么事?”何牧人冲着厅里叫了起来,他也不知道问谁。 众人面面相觑,悲凉无比的梁倩倏尔变得无比悲愤,霍地跳起来,激动万千又死气沉沉地望着何牧人。何牧人顿时脚生寒气,迅速漫身,直冲脑门,这不是他认识的梁倩。
曾经的梁倩,是一个动如脱兔,静若处子的洋溢着无限活力的窈窕淑女,现眼前这个梁倩,就像撒了野的泼妇,出了笼的母老虎,气势汹汹,仿佛一扑上来就能将他整个吞了。 “何牧人,你回答我两个问题。”梁倩又往前窜了两步,逼近何牧人,嘶哑地叫道。 何牧人目光深沉,闪烁着无限哀伤,不说话。梁氏也紧张地站了起来,担心梁倩又做出过激的事情。刘财来夫妇像看戏般,很是淡定,都斜着头颅,不看何牧人,只望着梁倩。 “我问你,你是不是在乐会老家,成过一次亲,媳妇被抢走了?”梁倩咬紧牙关地问道。 何牧人一阵惊谔。他不明白梁倩怎么问起这个被他珍藏多年,却从不易去动它的往事,而她到底又从哪里得知他这个秘密。在海口城,除已故的郑老先生和郑兰兰,连汪兴都一知半解,只知他是孤儿,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你说呀!”梁倩嘶哑着声音叫道,她的确是疯了,歇斯底里的又流出了眼泪。 何牧人只有沉重地点点头。 “我再问你,郑兰兰生的儿子,是不是你的种?”梁倩又一阵嘶吼,她觉得问这话时,内心一阵作呕,有一股无比强大的秽物来势汹汹,企图冲破喉咙,一泄如注。
但她不是梁安,她猛捂着胸口,狂吞口水,硬是将秽物逼回了肠道。 何牧人两眼迷茫,悲哀地说道:“这个我根本无法回答你。我从来就没问过,也不敢去问,我怕伤害她。” 梁倩过激的语气却突然变得苍白无力,晃了一下,指着他叫道:“懦夫,骗子,你滚!” 梁倩说着,只觉一阵晕眩,如踩石悬空,摇摇欲坠。梁母见势不妙,上前抱住她,扯着老母鸭的嗓音,哭吼道:“你还不快滚,难道要害死她不行?” 何牧人心血汩汩,僵硬不动。他只觉心脏仿佛被毒蛇猛兽狠咬撕烂,想挣扎又无能为力,想哭号又喊不出声。 天地寂然,心冷似冰,何牧人像一个被冰封千年的尸体,只保持着原来的表情,傻傻的,痴痴的,呆呆的,悲怆无比,绝望异常。这时,一直阴沉不动的刘财来,站了起来,走到厅门前,一边推着何牧人向梁氏宅门外走,一边轻声低语地说道:“何老板,有些误会是不能一时说得清楚的,听我的话,还是先避一避,等她心情好转,再来说说?” 何牧人如一具僵尸,神情麻木,又让人无不退避三舍的,在诸多闲人戳戳点点的窃窃私语中,离开了大街。他像上帝迷途的羔羊,神不守舍地不知往哪里去,也好像没有地方可去。
然而他双腿像受了什么指点,向横沟溪方向步履艰难地走去了。 他站在横沟溪渡口,眼前苍苍茫茫,溪水静止,白云不动,风无声息,大地陷入了一种可怕的空洞死寂状态。他就这样站着,不叫也不动,眼珠深陷,远望像被挖空了似,阴森恐怖。 不知过了多少个千年,他像一条冰冷的河流,被灰冷的阳光照射着,慢慢解冻。他思维动了一下,双眼眨了一下,灵魂终于回窍了。这时,他却发现摇头爽正立于船头,孤独一人,充满敌意与复杂的表情望着他,不说话。 横溪沟像一条死河,新埠岛像一座死岛,而僵持对立的这两个男人,就像是准备拼命的生死之敌。而他们决斗的战场,仿佛就在船上。何牧人僵硬地上了船,立于船头,摇头爽却拿起长长的竹篙,走到了船尾。 船不知道什么时候过了溪,何牧人还是一动不动。良久,摇头爽终于沉不住气了,很冷漠地说道:“何老板,该上岸了。” 他知道,何牧人渡河,只有一件事,就是找她的婆娘郑兰兰。如果不是他之前救过郑承谰,他早就一竹篙将这男人打下水,但是他想了想,还是忍住了。 何牧人似乎缓过神来了,转头望着摇头爽坦胸露骨,左右不由自主的晃动头脑,涎水连连,他心里更加的悲哀绝望。
如果不是因为他要闯南洋,郑兰兰怎么过下嫁这个牛鬼蛇神般的贱人,如果不是因为他一念之差,播下火种,郑兰兰又怎么愿意狠心赌气将自己一生的青春,主动埋葬在这个乱岗烂泥般的男人脚下。 摇头爽久久被何牧人诡异的眼光盯着,原来沸腾的时刻准备干架的激情,像被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毛骨悚然,浑身起了鸡皮疙瘩。他抹了一嘴涎水,大声咳嗽,叫道:“你要不要上岸?” 何牧人转头前后望望,大地诡异,不见人影,风似乎动了,拂过他的刺痛的眼睛。何牧人仿佛在寻找着什么,想了半天,终于面对摇头爽,说道:“我就问你一句话?” 何牧人语音虚幻,轻得像一片浮于水面随波逐流鹅毛,摇头爽耳朵灵敏,还是听到了。他肃然紧身,等着何牧人的问题。 何牧人问道:“郑承谰是不是我儿子?” 摇头爽骤然变色,青一阵,黑一阵,青黑不分。
他猛然跳起来,指着何牧人吼道:“你胡说!” 何牧人摇摇头,绝望地说道:“我也希望我是胡说。可是他们都说,那是我的种。” “谁说的?是不是李秋霜那老婆娘,她还跑来问过我,我把她吼回去了,难道还不甘心吗?”摇头爽声音凄凉尖厉,像坚守阵地的猛兽,不容他人越雷池半步,侵入自己的领地。 何牧人怒力控制着内心的悲哀,又说道:“这个问题压我好久了,今天咱们就一次说清楚了吧。” 摇头爽两眼喷火,怒声狂骂道:“这些多舌妇,欺负我阿爽不长****吗,我****强大得很,信不信我一****戳死她们。” 何牧人不睬摇头爽那些污言秽语,死死地盯着摇头爽,正色问道:“你说,郑承谰是不是我的种?” “****你个祖宗,敢欺负老子。”何牧人话语刚落,摇头爽一竹篙拦腰猛击过来,他身体晃了晃,只见摇头爽又叫嚣着狂扑过来,一边叫着,“****你个****,敢跟我抢儿子,跟你拼了。
”骂着,摇头爽已经冲到何牧人面前,将他抱住,滚下水里。 俩个精通水性的男人在水里打起了水仗。摇头爽再展昔日雄风,拿出过去跟梁安干架的猛劲,保护做为男人的尊严和爱情的硕果,他双手抓住何牧人头颅,死死按于胯下,仿佛要让对方好好见识他的****。何牧人劲腿往水底一蹬,三百六十度翻转,一腿冲出水面踢中摇头爽头部下巴,一腿直撞摇头爽胯下的****。大头小头一齐被撞,摇头爽不知是下巴痛,还是****痛,啊的一声怒喊,松开手,沉到了水里。横沟溪都被他们搅浑了,何牧人又腾身一跃,骑住摇头爽的头颅,死按住压在水底,摇头爽就像一头扎到水里的饥渴的牛,咕噜咕噜的,横沟溪上游漂来的尿水畜水,都被他一通的灌进了肚皮。 那场水仗打得惊天动地,鬼哭狼嚎。他们从水里打上岸上,又上岸上打下水底,都逼红了眼,踢腿扬手,漫天怒吼,你追我赶,沉寂的大地顿时变得生动活泼,精彩纷纭。
海鸟充当裁判,在遥远的天上吹着口哨,迅疾的阵风吹得天上云卷云舒,溪里的鱼也沸腾了,不停的蹦出水面,为他们加油呐喊。他们无边无际的嘶打声,惊醒了遥远的村庄。郑兰兰闻声赶来,她拉着郑承谰跌跌撞撞地跑来,风好像都要刮倒她,她远远地就看见,俩个像公牛斗架般的男人一个揪着对方的耳朵,一个抠着对方的鼻子,一个抓着对方的腿,一个扯着对方的头发,像是连体人,你缠着我,我绕着你,难分难舍,如胶似漆。 郑兰兰悲极而鸣,仰天而哭:“住手!” 这才是真正的裁判,俩人都不禁松手,都喘着粗气不服气的退后了一步。裁判郑兰兰一头扑到摇头爽怀里,慌张地抚摸着,像抚摸着一件丢而失得的稀世珍宝。倏尔,只见她咕噜地爬到何牧人面前,猛地朝沙地上嗑了一个头,狂哭道:“求求你,放过我们全家吧。” 何牧人如晴天霹雳,跪倒于地,嚎叫着也向郑兰兰猛烈嗑头。郑兰兰嗑一头,他嗑两头,郑兰兰嚎一声,他嚎数声。最后,俩人都双双晕倒在那片,无比纯洁的无比荒凉的无比悲情的沙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