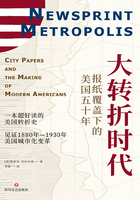一 槟城,又称槟榔屿、槟州,位于马六甲海峡,因盛产槟榔树而得名。十五世纪初,马来半岛建立了统一的满刺加(亦称马六甲)王国,十六世纪初,马来半岛却成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葡萄牙,荷兰,英国人先后染指其地。到了十九世纪末,大英倚仗日不落帝国国力,将东马及西马收为囊中,于是马来半岛彻底沦为英国的地盘。 不知何时,槟城成了冒险家的乐园。除了西方诸国外,中国人作为东方的挨打者,更是不甘寂寞,群涌而来,参与游戏博弈。然而他们多是以劳工名义前来掘金,头脑灵活,发财致富,混成上人上人的,可谓凤毛麟角。 我们海岛琼州府人是继福建人和广东人之后,登上马六甲海岸觅食的,较为之晚,所以势力单薄,不成气候。然而当我的老祖宗何牧人这代追梦人一踏上槟榔屿时,一切都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那时,深秋的海面变得异常冰冷沉静,然而何牧人的心潮则日夜奔腾翻滚,犹如火煮。之前,他知道郑兰兰恨之入骨,躲着不见,无奈之下咬破指头,写下血书,以此明鉴。他想告诉她,他是爱他的,但他不得不选择远行。
无助的爱役使心灵,让何牧人彻底难眠,无法释怀。然而这种记忆带来的痛苦,随着他在海上漂泊的时间长久,似乎有所减弱。他突然想到,当前要面对的不是无穷无尽的情债,而是生存。船一旦登岸,他到底何去何从,根本没个底儿。 郑佑承早知道有他这么一天受苦的,临走之前又给他塞了几百两银子,以防后患。可银子总有一天要花完的,他既然选择远离,就要勇敢破冰前行,没有退路。与其拖着一具活尸回国,与其平庸苟活于世,不与现在就跳进这海,淹没在这汪波大海。 一股无所畏惧的心情,立即涌上他的心头。他在船上数夜未眠,海上惊奇的现出弯月,那缈小而苍茫的弯月,犹如他内心膨胀的欲望,夜夜在海里变得圆润。月光仿佛点燃了希望,他突然想起了一个人。 何兴林!! 念想如电,刹间就在他心头定格了。他想起族叔何兴林与他离别要闯南洋时,曾说要去马六甲。如果命运真要将他俩捆绑一块,就应该让他们俩相遇…… 这个貌似缈茫而又兴奋的念想,伴着何牧人在海上漂流数日。于是,他一登岸就问路,直奔琼州会馆,打听何兴林下落。
结果出人意料,会馆的老乡告诉他,他们并不知道这个人。 何牧人掏出一张纸条,问老乡知不知道这个地址。老乡告诉他,那是一个法国人经营的橡胶园,向东走三十里路就到了。何牧人兴奋极了,他问的就是阿麻子藏身之处。王阿六还算长眼,没有忽悠他,如果真能寻到陈麻子,也不枉此行了。 然而何牧人并不急于去寻仇,而是在槟榔屿大街小巷到处乱逛,熟悉人文地理。过了数日,他把身上大部分银子拿出来,到黑市买了一把毛瑟短枪。 在那一刻,他仿佛又找回了曾经上雷公岭复仇的激情,浑身顿然骚动。 数日后,何牧人潜往法国人的橡胶园。橡胶园地势复杂,位于数座大山之间,放眼望去,莽苍之色,映于眼底。何牧人爬上山顶俯瞰山下,顿然神情恍惚,山林之间,只闻鸟叫,不见人影,这到底是个什么鬼地方? 何牧人决定潜到园里瞧个究竟,发现橡胶园里人去林空,一片静谧。不会是上了王阿六的当吧? 可他又转念一想,或许是自己走错地方了?于是他决定找个人问个究竟。寻了半天,终于见到一间茅寮,走近一看,只见两个中老年华工,正懒懒的抬眼看他。
何牧人连忙从怀里掏出一包洋烟,笑嬉嬉的走向前去,问道:“老乡,打听个事儿?” 那中年人略胖,眼睛臃肿,表情呆滞;老年人瘦小,像被机器榨过的甘蔗,只剩下了皮包骨。他们一见何牧人手里的烟卷,眼睛乍然一亮,那中年人抬眼问道:“你哪里来的?” 何牧人小心翼翼地说道:“我刚来马来半岛觅食的华人,敢问两位大哥大伯也是华人吧?” 那中年人应声叫道:“华人多着很,小兄弟哪省的?” 何牧人利落的答道:“我海南岛的。” 那中年人有如电击一般,惊讶地叫道:“小老乡,你大老远的单独一人跑这干嘛?” 何牧人假装苦笑道:“初来乍到,觅食不易,想托熟人找个工作。我朋友姓陈,外号叫麻子,人称陈麻子,不知诸位知道这人不?”何牧人一边说着,一边把烟卷一人一支发到他们手里。 “陈麻子?”俩人异口同声叫道,不由警惕地盯着何牧人,接过的烟都不敢凑到嘴边。
何牧人惊喜地叫道:“大哥大伯,你们真认识这家伙?” 那中年老乡不由狐疑万分,上下打量道:“你跟陈麻子是啥子关系?” 何牧人见对方虎视眈眈,将计就计,只好忽悠道:“是道上的朋友,现在走投无路,想来投奔他。” 俩人一听,似乎放松警惕,中年老乡说道:“既然你是他道上的朋友,咱们又都是老乡,告诉你也防。我们胶园休割,陈麻子领了一群人去开锡矿去了。” 何牧人心头狂喜,按耐不住地问道:“哪里的锡矿?” 中年人伸手左指,说道:“二十里之外,有一座法国人开的锡矿,去那里问问吧。” 何牧人心肉直跳,一古脑的把烟卷塞到中年人手里,激动的说道:“多谢大哥,后会有期。”说着转头就跑出去了。 不一会儿,何牧人突然折身返回,焦急地问道:“大哥,可否向您再打听个人?” 那中年人拿了他的烟卷,手也软了,爽快地应道:“你问吧。” 何牧人忙问道:“您知道有一个叫何兴林的吗?乐会县人。” 中年人一听,疑虑地望着他,问道:“你今天走的是什么****运,好事全都被你问中了。” 何牧人悬浮的一颗心几乎都要爆炸了。
他惴惴地问道:“大哥,你真知道我叔的下落?” 那中年人瞪大眼睛问道:“何兴林是你叔?” 何牧人兴奋地点点头。 中年人指着身后的茫茫大山说道:“何兴林就在橡胶园里。可是这小子对橡胶园着了魔,长期云游其间,不知去向。等他回来时,我给你捎话。” 何牧人不知是紧张还是兴奋过了头,眼皮子真跳,拱手说道:“多谢大哥,他若回来,烦请转告他,族人何牧人过段日子再来找他。” 说完以后,昂头离去,走出大山,朝锡矿的方向奔去。 万里越洋,追杀仇家,这事要广而传之,那是何等英雄悲壮之事。然而何牧人怎么也没料到,他复仇心切,没有等见到何兴林一面,持枪孤身寻找陈麻子,不幸的把自己送进了虎口。 所谓的锡矿,位于槟榔屿一座小岛上,这里四面环水,有河从中间穿过,河边驻防着法国人及他们的走狗,日夜巡逻,防备外逃。夜凉如水,星空暗淡。何牧人悄悄地潜往这座无名小河,趴于一堆草从灌木中,眺望着对岸的无名小岛,心潮如水,暗起波澜。 对岸黑灯瞎火,阴森恐怖,闻不到一丝人气,仿若鬼岛。若不是白天亲眼侦察,谁也不相信那孤岛上,有数百劳工,被上下驱赶,开挖锡矿。
何牧人像一只狡猾的夜鹰,一动不动,一直伏于草从中,熬到了下半夜。 天地之间,莽莽苍苍。等到四周的虫子都没了声息,他则像一只离岸的鳄鱼,无声无息的爬出,潜入水里。夜半的河水仿佛被冰霜泡过一般冷极了,为了适应这水度,他不得不潜于水底浸泡起来。 何牧人精心选取这一片潜伏之地。河面并不宽广,河水也不算浅,做为长年泡在故乡的万泉河里泡水长大的人,一口气游到对岸的小岛,简直是小菜一碟。 过了片刻,他悄悄伸出水面,大呼一口气,然后又潜到水里,就像河底潜着大鱼,只见水面泛起缕缕波痕,向对岸滚动。 “咝——”何牧人两手摸到了岸边的水草,轻轻地抬头,伸出嘴巴,向天空吐着水气。吐完水气,他睁眼扫视,借着朦胧视力,发现小岛犹如牧场,全被高柱铁丝合围封锁,无边无际。 何牧人心头冷笑,爬到岸上,耳朵贴在地上,听了一会儿,没有声息,才放心的掏出一个铁钳像老鼠啃树般,不稍片刻就啃出一个大洞。他抬起身来倏的一声,就溜了进去。 天渐渐的亮了。红通通的太阳像泡在海里的大蛋黄,正被人湿漉漉地打捞上来,透着寒气,铺天盖地,小岛被染红了一片。小岛虽小,五脏俱全,山丘树林此起彼连,一望无涯。
何牧人摸索了一个晚上,终于找到了一个有利观察的位置,趴在一处高丘,放眼望去,山下平原之处,一览无余。 他发现前方不远处,有若干工棚,工棚有一处正向上冒着炊烟,工人陆续起床,僵硬地从煮伙食的营房里,端着早点,蹲到棚外的空旷处各自吃着。 远远地望去,没有生气,没有喧哗,像是被驯服的畜牲。 工棚数步远处,还搭建数座高脚遮阳楼阁,数个外国鬼正端着枪,在上面走来走去,有人嘴还叼着粗笨的雪茄,像是啃着他们的早点。 过了好一会儿,突然空中响起一阵刺耳的哨声,有个声音从人处房屋里走出吼道:“集合,集合,出工了。” 何牧人远远的听着,心里不由震了一下。他的耳朵仿佛是天线接收器,对着冥远天空,任何声响都逃不过他的捕捉。他再侧耳旁听,那声音又在一个劲儿地叫喊道:“快点,快点。” 这么一听,何牧人的心几乎都要蹦出胸来了,那个声音绝对是陈麻子。要不是他,他下辈子做牛做马,做猪仔被卖南洋来。 何牧人既兴奋又激动,神情不由晃乎,只觉热血沸腾,浑身颤抖。过了一会儿方才回神,他从怀里掏出一个西洋望远镜,朝那叫喊声望去。
这下子他终于看清楚了,那个趾高气扬的叫喊声,确实就是陈麻子! 岛上天气阴凉,何牧人却觉全身燥热,额上渗出汗水,咸咸地流进了他的眼睛。他抹了一脸汗水,再睁眼远望,只见陈麻子吹着口哨,走到一巨石上,不断的挥手驱人。工人们在他的驱使下,拖着僵尸一般的身体,集合成队,朝着一处山谷走去。 狗还是改不了****的本性。一想起自己差点沦为眼下这其中一头猪仔,何牧人眼中都要喷火了,心里不由狠狠地咒骂陈麻子。 这时,于高脚楼阁上蹲守的外国佬也拖着长枪下楼来,跟在工人们背后。
陈麻子哈腰一个个打个招呼,那些外国佬懒得睬他,挥挥枪就算是回礼。于是,陈麻子只好自讨无味的走在他们面前,跟在工人屁股后头走了。 望着陈麻子远去的背影,就像猛兽看着到嘴的猎物溜了一样,何牧人心里像着了魔,都要疯了。 尽管经历多年的苦难挫折,仍然不改老脾气。一身火气,意气用事,头脑动不动就冲血发胀。此时此刻,如果云冲鹤呆在他身边,可能都要端盆冷水来浇他。 何牧人快按不住自己了。然而一种莫名的理智又告诉他,不能轻举妄动,要沉得住气。云冲鹤仿佛又复活了,当年的话语又历历在目的浮在他耳边——冷静,冷静,再冷静。 他决定暂是窝在山丘上守株待兔,等待时机的出现和上天的眷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