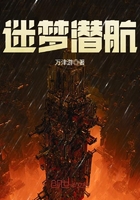卡夫卡的朋友费力克斯韦尔奇宣布订婚了,这并没有让卡夫卡振作起来。他告诉格蕾特,这意味着他"失去了一位朋友,因为一个结了婚的朋友不是真正的朋友"。卡夫卡看重的是一对一的亲密关系,现在却不得不面对可怕的"合伙关系"。另一方面,他和费力克斯定下的"单身汉同盟"解除了,他从中获得了解脱:"我是自由的;独自相处时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他希望成为的那个人。"在日记中,他更加坦白,承认费力克斯结婚让他很生气:"我仍旧独自一人,除非菲利斯还要我"。另一位朋友,布洛德决定把他的一部新小说《第谷布拉赫通往上帝之路》题献给"我的朋友卡夫卡",卡夫卡说,"很长时间以来我第一次感到纯粹的快乐……我被抬高了,竟然和布拉赫并排在一起,他可比我重要多了"。
事实上,卡夫卡因为菲利斯而深深地感到痛苦,他不但没有振作起来,而且有了自杀的念头。他想像着自杀的场景:冲向阳台,挣脱所有拦住他的手臂,然后纵身一跃,身后只留下一封遗书:"我跳楼是因为菲利斯,但即使她接受了我的求婚,对我来说也不会有多大改变。我只能跳下去,没有别的出路。我只是通过菲利斯才看清了自己的命运;没有她我活不下去,必须跳楼,然而--菲利斯也觉察到了这一点--和她在一起我也活不下去"。
2月27日,卡夫卡再也不能忍受了。他破天荒请了一天假,星期五晚上坐火车去了柏林,而他根本不清楚菲利斯是不是在柏林(令人费解的是,他仍然没有使用电话这种资源)。第二天早上,他直接去了菲利斯的办公室,请传达员给菲利斯递了一张纸条。等待的间隙,他一直盯着接线总机,"在我的事情上,它从来没有起过作用"。菲利斯对他的来访深感吃惊,但仍然很客气,她下楼来见他,午餐时间带他去了附近的一个小饭馆,在那里坐了一个小时。他和她一起回到公司,还参观了她的办公室,菲利斯下班后,他们又一起做了两小时的散步。晚上,由于工作上的原因,菲利斯不得不去参加了一场舞会,但是星期日上午他们在动物园里度过了三个小时,还去了一家咖啡馆。下午,她又忙着处理家庭事务,没能去车站送他,不过这次她发来电报表示歉意。
在卡夫卡看来,周末的柏林之行,菲利斯似乎"十分喜欢我",但还不到和他结婚的程度,"她对我们共同的未来有无法克服的恐惧;也许她不能适应我的特殊性格。"她告诉他,她从来不做拿不定主意的事。他坚持说,即使她觉得对他的感情还谈不上结婚,还是要对他的求婚说"同意",因为"我对你的爱是那么多,完全可以弥补这种不足"。卡夫卡担心菲利斯不够爱他,他甚至怀疑她实际上"有点讨厌我"。在她家的门廊前告别时,卡夫卡想摘掉她的手套吻她的手,她却做出"一幅充满敌意的怪相"。卡夫卡也很讨厌菲利斯的牙齿,她所有的牙齿都补过。除了这些半心半意的愿望,卡夫卡不大确定菲利斯对待文学在多大程度上是玩世不恭的,以及她准备如何面对布拉格的生活。她将会怀念在柏林的日子,怀念她的漂亮衣服,她不会喜欢火车的三等车厢、电影院的便宜座位以及其他种种廉价的东西,她是一个物质女性。
这个时期,她表现得非常友好(尽管如此,卡夫卡仍然有些担心,她本来是一个健谈的人,但和他在一起的七个小时里,她几乎没有说过一个完整的句子)。她和他手挽手散步,即使在其他人面前也用"你"称呼他,她的纪念品盒里珍藏着他的小像,她说她希望保留他的信件和照片,并且很乐意继续通信。但是他们都没有谈到结婚。在返回布拉格的途中,卡夫卡在德莱斯顿火车站给格蕾特寄了一张明信片,卡片背后潦草地写着:"不可能比这更糟了。接下来就该是刺刑了"。
在柏林时,惟一的安慰是他第二次见到了马丁布贝尔。卡夫卡把这次见面看作是"我对柏林最纯洁的记忆,这种记忆成了我的避难所"。除此之外,这次柏林之行就完全是一场灾难了。为了避免彻底崩溃,卡夫卡下定决心,如果他不能同菲利斯结婚,他就要辞去在保险公司的职位(或者申请长期离职),前往柏林,尝试着做一名新闻工作者。他要去的柏林是画家恩斯特路德维格基尔希纳笔下的柏林,后者在这一年完成了那幅著名的《波茨坦广场》。奥地利小说家弗莱什冯布鲁宁根曾在一年前写道:"你必须认识到,对我们这些在维也纳的人来说,柏林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说,柏林是疯狂的、堕落的、都市化的、缺乏特色的、巨大的、未来主义的。它是文学的、政治的、艺术的(那里是画家之城)。简而言之:它是地狱粪池和天堂的结合体。"卡夫卡没有选择这个令人狂热的大都市,而是留在了布拉格,他切断了自己另一条逃亡的道路,尽管他对柏林一直念念不忘,并在生命的最后一个年头终于移居那里。但是此时,1914年的上半年,他感到"菲利斯使我完全迷失了",他需要寻找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