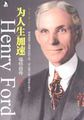卡夫卡还有一篇小说与《地洞》遥相呼应,这就是写于1922年秋的《一只狗的研究》。当时,卡夫卡从普拉纳返回了布拉格,身体状况很糟。在这篇小说中,叙述者同样是一只动物,他发现他自己"离群索居、孤独寂寞、仅仅从事我的小小研究……我们彼此远远地分散生活,忙于各自那独特的、连离得最近的狗都无法理解的消遣。"小说叙述者的这番话与卡夫卡的自我剖析非常相似:"近来我开始越来越多地回顾我的生活,寻找我可能犯下的决定性错误,寻找所有这些麻烦的根源,但我却怎么也找不到。然而我必须这样做,否则的话,假如我努力终生却仍然不能获得希望获得的,那将会证明我所希望的虚妄,随之而来的就是彻底的绝望。"
1924年初,卡夫卡给罗伯特克洛普施托克写了一封信(当时后者仍然在布拉格从事医学研究),信上说:"关于我本人没有什么好说的……要是我能挣钱该多好!但没有人会给一个中午十二点还卧床不起的人付薪水"。在1924年的柏林,卡夫卡终于明白生活的艰难,他对克洛普施托克讲了一个朋友的故事。后者是一名画家,但迫于经济压力不得不在路旁摆起了书摊,从早上十点到太阳落山一直站在大街上吹冷风。"圣诞节期间他每天能挣十个马克,现在每天只能挣三四个马克"。克洛普施托克手头并不宽裕,但他总是挂念着卡夫卡,还从布拉格给他寄来了巧克力。这个年轻人真诚的情感和纯真的理想让卡夫卡感动,他安慰前者不要因为经常给他写信而自责。两人之间来往的书信很多,克洛普施托克曾随信寄了一本克劳斯主编的杂志《火炬》,卡夫卡很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晚上忍受病痛折磨的时候"沉浸于"阅读克劳斯的狂欢"中了。终于,格龙内瓦尔德公寓下了逐客令,"因为我是一个穷困的外国人,付不起房租"。2月1日,卡夫卡和多拉搬到了海德大街25~26号的策伦多尔夫公寓,女房东是已故新浪漫主义作家布塞博士的遗孀,这位老派的作家如果在世,"一定会非常反感"卡夫卡的现代性。卡夫卡觉得,女房东的丈夫阴魂不散,搬到这套公寓实在并非明智之举。"虽然如此,我还是要搬过去;世界上到处都充斥着危险,假如眼下的危险是从所有那些未知的危险中来的,那就让它来吧",他这样对费力克斯韦尔奇说,后者定期给他寄送布拉格周报《自卫》。搬家那天,卡夫卡"虚弱、发烧,已经连续四个月没有在晚上出过家门了。"
2月底,策伦多尔夫公寓里来了一位探望者:乡村医生齐格菲尔德略维舅舅。卡夫卡的情况让齐格菲尔德大为震惊,他极力劝说外甥离开柏林,去一家疗养院治疗。当时卡夫卡的体温一直高居在华氏一百度以上,尽管如此,他一开始还是不同意舅舅的建议,他不愿离开策伦多尔夫公寓,因为在那里他可以坐在阳台上沐浴早春的阳光。然而,持续的高烧使他只能待在屋里,连出去散步都成为不可能了,他开始明白自己必须要采取一定的对策了。"然后我想到,在本该享受自由的和暖季节里,我将会失去自由,这让我又一次深感恐惧。但是,紧接着我开始早晚连续咳嗽几个小时,每天几乎吐满满一瓶--这又为去疗养院找到了理由。然而随后又是恐惧,比如,一想到那种地方强迫病人吃的食物就害怕"。
这个时期,卡夫卡同以往一样写了大量的信件,但他的身体无疑越来越差了。尽管卡夫卡以往同父母的关系并不亲近,但他从柏林写给他们的信却非常感人,在一封信的结尾,他问:"你们今晚都睡在哪一个房间呢?"在另一封信中,他告诉父母不该善待这个"漂泊在外"以自我为中心的儿子(他们给他寄来了冬衣)。他让他们不要给他打电话,因为现在接电话对他来说已经相当困难了--如果电话铃响的时候多拉碰巧不在家,那该怎么办呢?卡夫卡的父母肯定能从这一点了解到他的身体是多么虚弱。3月1日,他又给他们写信说,如果去疗养院,他就会失去"安静,自由,阳光充足且通风透气的公寓,愉快的主妇,好心的邻居,同柏林的亲近以及刚刚到来的春天",但他知道他必须得走了。在从柏林写给他们的最后一封信中,他对父母寄来的冬衣表示感谢:"没有马甲,真是一个奇迹,这么漂亮又这么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