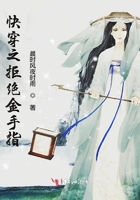10月,奥特拉对哥哥健康状况非常担心,她背着卡夫卡去见了保险公司的经理,劝说后者给卡夫卡延长病假。保险公司要求卡夫卡亲自去一趟,他照办了。公司准许他继续休假。他开始考虑去格里门施泰因疗养院或维也纳森林疗养院,这两家疗养院分别位于维也纳向南六十千米和八十千米处,他可以从那里去看米伦娜。但他下不了决心,内心十分痛苦:"我没有力量起程;一想到站在你面前的情景,我就预先觉得自己无法承受,无法承受脑子里的压力"。他绝望地说,没有人能理解他的处境,就连米伦娜也不能:"在我周围的环境下像人一样生活是不可能的;你明白这一点,但你仍不愿相信。"他甚至为自己写给米伦娜的信而绝望,在他看来,那些信带来的只是"误会、耻辱,几乎不可磨灭的耻辱",这使他越发感到无能为力,似乎它们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强大声音"在对他说话,"那仿佛是你的声音,要我沉默"。最终,那些信"只是折磨,来自于折磨,也只能造成折磨,不可救药的折磨……这有什么用呢?保持沉默,这是惟一的生存方式。"
然而,当他走在布拉格的大街上,"笼罩在反犹太人的气氛中",听人们称犹太人为"肮脏的暴民",他不禁想:"离开这备受歧视的地方难道不是合乎自然的吗?(而犹太复国主义或民族情感在这里是没有必要的。)那种非待在这儿不可的英雄主义像是浴室里消灭不掉的蟑螂一样。"
卡夫卡的研究者们就这里所用的"消灭"一词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辩论的主题是卡夫卡在多大程度上"预见"到了纳粹德国实行的种族灭绝政策。从表面上来说,他不大可能预见到这一点,但是我们也许不应该只停留在表面。卡夫卡理解他所处的时代和这个时代的黑暗面。他描写的杀人刑具、恶梦般的残酷的极权统治,以及他对犹太人命运的深刻理解,对此我们无法仅仅做单纯的解读,因为作为读者,我们了解后来发生的那段悲惨的历史。卡夫卡是否预见到了这一切?对这个问题我们无法作答。这是一场没有结果的辩论,但与此同时,它又总是萦绕在我们的心里。在1920年11月中旬的那一天,卡夫卡从奥培尔特公寓大楼的窗户向下看到那些真正的暴民,纵马横行的警察和手握刺刀的宪兵,他觉得待在楼上的房子里,"总是在保护下生活,是一种令人厌恶的耻辱。"那么,哪里才是他的归宿,他的安身之处呢?
1920年12月13日,卡夫卡又得到了三个月的病假,他决定去约兰福尔贝格尔夫人的肺结核疗养院休养一段时间,这所疗养院位于斯洛伐克的马特利阿里山上。格里门施泰因疗养院已经给他发来了正式的住院许可证,但他改变了主意,于12月18日出发前往马特利阿里,打算一直住到1921年3月20日。11月,他曾对米伦娜说,他之所以不想去维也纳,原因之一是他咳嗽得厉害,每天晚上从九点四十五到十一点他都会一直咳个不停,隔一个小时后,凌晨一点他又会接着咳嗽起来。因此他觉得自己不能住卧铺车厢。尽管如此,从布拉格出发到马特利阿里的旅程却并没有那么糟,让他有点懊恼的只是行李在路上耽搁了很久才运到。
火车到站后,疗养院的人驾着雪橇来接卡夫卡,载着他在月夜下穿越大雪覆盖的森林,走过了一段美丽的行程。从外表上看,马特利阿里疗养院"光线黯淡,条件很差",冰冷的大厅里空无一人,驾雪橇的人跺着脚喊人,好一会儿才出来一个女仆,她带卡夫卡去了二楼的两个房间,房间是在海拔九百米的高度上用木架涂抹灰泥建成的。卡夫卡的房间带一个阳台,隔壁的房间则是给奥特拉预定的,按计划她不久会来这里和卡夫卡会合。进入房间后,卡夫卡惊愕地发现炉子里冒着呛人的浓烟,铁床上没有床单,衣柜的门坏了,通往阳台的仅仅是一道单层的简易门。女仆尽最大的努力收拾,想让卡夫卡高兴起来,但卡夫卡觉得这里的条件还远远比不上谢列森公寓。